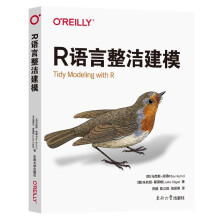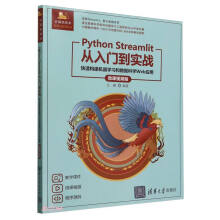在《吉姆老爷》中,马洛根据信件、一个不完整的文本、极具有偏见的证人(比如布朗这样的绅士,他痛恨吉姆,并且欲置他于死地),以及吉姆遭受了创伤的情人珠儿等线索拼凑成关于吉姆死亡的故事。此外,马洛对于帕特桑片断的不完整叙述,这可能是因为吉姆死亡的时候他并不在其身边的缘故,而非出于想对读者掩盖叙述事件这样一种内在的动机。读者感觉到马洛对事件本身的理解是令人信服的,尽管马洛内心里将吉姆看作“我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他对于吉姆置下沉的“帕特娜”号船只于不顾这一表现深感失望,这两方面都定然对其故事讲述的方式产生了矫饰作用。但是他所获得的信息是令人怀疑的。的确,关于吉姆老爷的很多戏剧性的事件都是源自于马洛为理解他所讲述的这位年轻人的性格而所做的各种断断续续的努力。此外,读者可能会推断,一旦马洛见证了吉姆的死亡,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向与他一同进餐的听众和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且更符合常理的讲述。<br> 为了判断一位叙述者从何种程度上讲属于易犯错误的这一类型,读者必须思考叙述者是在何种程度上在他所获取的信息以及对于该信息的理解上出现偏差。叙述者是连续不断地犯错误吗?我们能否设想出叙述者会准确无误地报道信息的各种情形?一旦我们能够设想出一位已经长大成人的哈克贝利,他知道那位寡妇的“嘟嘟囔囔”实际上是在做饭前祷告,也明白他撕毁给华生小姐的信是一个正确决定;一旦我们能够设想出一位马洛,他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也作了更多的思考,能够更为清晰地讲述对于吉姆生死所蕴含的意义,我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所遇到的哈克和马洛是易犯错误的叙述者,而非不可信的叙述者。<br> 要说明不可信的叙述者,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中的叙述者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不可信叙述者的例子,而莫尔·弗兰德斯则可以作为一个不那么典型的例子。和《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泄密的心》中,叙述者在故事的开篇就不乏很多矛盾之处。爱伦·坡的叙述者反复强调受述者指责他的疯狂状态(往往是一个关于精神稳定性的明确信号):“千真万确!——神经紧张——一直以来我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神经紧张状态。现在仍然如此。但你为什么要说我是疯狂的呢?这种疾病加剧了我的各种感觉——而不是消除了它们——也没有消减它们。”(第792页)为了理解这种叙述,读者要迅速地对这种精神上的不稳定性和不可信性追根溯源。这样,叙述者就会被诊断为属于病态的不可信性,而读者也会因此选择治疗性的策略,对文本中的细节进行反向解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