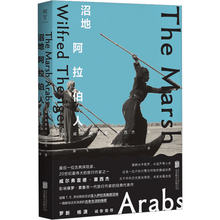萨拉起床很晚。已经十点多了。气温没变过,还是热。每天早晨总是要过上几秒钟才想得起来大家到这里是来度假的。雅克还在睡,女仆也是。萨拉走进厨房,吞下一碗冷咖啡,走进游廊。孩子总是第一个起床。他全身赤裸着坐在游廊的台阶上,正监视花园里壁虎的走动、河里小船的行驶。
“我要去乘汽艇,”他看到萨拉时说。
萨拉答应他。孩子说的有汽艇的那个人来了才三天,谁都还不怎么认识他。可是萨拉答应孩子要带他上这艘汽艇。然后她到浴室找来了两罐水,给孩子淋了好一会儿。他瘦了一点,面有倦容。夜里谁都得不到休息,就连孩子也是。这两罐水用完,他要再来几罐,然后还要几罐。她去取水。他在凉水下笑,复活过来了。淋浴一完,萨拉就要给他吃中饭。在这里,孩子从来不太急着吃东西。这个孩子爱喝牛奶,牛奶在这里一过八点钟就变酸。萨拉冲了点淡茶,孩子机械地喝着。给他什么他都不吃,又去盯着小船和壁虎看。萨拉在他身边待了一会,然后决定把女仆叫醒。女仆嘟囔了一声,没有动。这与别的一样说明天热,萨拉也不比叫小孩吃东西那样更坚持。她淋浴,穿上一条短裤和短袖衫,接着因为大家都在度假,她也就没事可做,除了与孩子并排坐在游廊的台阶上,等待他们的朋友吕迪到来。
河在离别墅几米远的地方流过,宽阔色浅。路沿着河流一直延伸到海边,远处汪洋一片,油光光的发乌,笼罩在奶白色的薄雾中。这块地方惟一美丽的东西就是这条河。地方本身,并不美。他们到这里来度假就是因为吕迪他喜欢。这是海边的一个小村子,——西方国家年代悠久的海,是世上最封闭,最炎热,最多历史沧桑的地方,不久前还在海边打过仗。
因而,三天以前,确切地说三天加上一个夜晚以前,一位青年踩着了一枚地雷,在山里,就在吕迪的别墅上方。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那个有汽艇的人来到了酒店。
这座山的山脚下,沿着那条河,有三十幢房子,一条七公里长的土路把它们跟其他地区隔开,路在这里的海边停住。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的。这三十幢房子每年住满了来自各国的夏日旅客,这些人都有这个共同点,就是吕迪在这里才把他们招引过来的,他们相信大家都爱在这些荒野度假。三十幢房子和沿着房子前仅仅只有一百米的碎石路。吕迪说他喜欢的就是这个,雅克说他不讨厌的就是这个,这地方什么都不像,那么偏僻,以后毫无扩展的希望,由于山太陡峭,河又太近,萨拉说她不喜欢的也是这个。
吕迪和他的妻子吉娜十二年前来到这里。他还是在这里跟她认识的。这事已有十二年了。
“汽艇,”孩子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
只有这个人是偶然来到这里的,不是因为吕迪的缘故。一天早晨他乘了他的汽艇来的。
“等一天我们上那艘船去,”萨拉说。
“哪一天?”
“不会多久的。”
孩子全身淌汗。这年夏天全欧洲都热。他们到了这里,也在受夏天的罪。在这座山脚下,山太近了,萨拉觉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她曾对吕迪说:
“我肯定就是对岸也会凉快些。”
“我在这里待了十二年啦,你一点不了解这地方,”吕迪说。
雅克对两岸的区别没有意见。对萨拉来说,那里夜夜显然会有清风吹起。对岸确实有二十公里的平地绵延到山前,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扫雷员的父母就是从山那边过来的。
她去取水,给孩子湿了湿额头。他很开心让人这样做。三天以来,事故发生以来,萨拉避免去拥抱孩子。吕迪到的时候,她给他穿衣完毕。那时十一点钟刚过。雅克还在睡,女仆也是。吕迪来后,孩子换了游戏。他开始在她刚才给他洗澡的地方玩沙堆。
“早上好,”吕迪说,“我来看看你。”
“早上好,吕迪,你可以去把雅克叫醒了。”
吕迪抱起孩子,咬他的耳朵,把他放在地上,走进雅克的房间。他一进去就打开护窗板。
“现在还不起来,你什么时候游泳?”
“那么热,”雅克说。
“比昨天要好一些,”吕迪说,语气很肯定。
“你什么时候才不会拿人开玩笑。”
吕迪不会为热叫苦连天,就像一棵无花果树,就像那条河。他让雅克醒来,自己出去跟孩子玩。萨拉站起身,梳头。吕迪说到汽艇的魅力,说它开得跟汽车一样快。他也如同孩子那样很想上那个人的船。听到他说话,突然萨拉想起吕迪说过她的那些话。现在已有八天了。有一天晚上,在一场争吵时,雅克把这些话说给她听。那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后的第一天——除非是在争吵时她听到了吕迪说过她的那些话——山上发生了那桩事故。在这个早晨以前,她没有时间去想吕迪说她的那些话。由于山上出了事故,也可能是由于那个人和他的汽艇来了。
“你跟我们一起游泳去吗?”吕迪问。
“我不知道。哦,,说到这儿,他们一直还在山里吗?”
有两天三夜,扫雷员的父母在捡他们孩子的尸体残片。有两天他们固执己见,坚信还有没捡到的。只是从昨天开始他们不再寻找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离去,没有人清楚这是为什么。舞会已经取消。全镇哀悼。大家在等待他们离开。
“我还没有去过,”吕迪说,“但是我从吉娜那里知道他们还在。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们拒绝在死亡报告上签字。尤其是那个母亲。三天来要求她签字,她连听都不听。”
“她没说为什么吗?”
“好像没说。你为什么不跟孩子去游泳?”
“太热了,”萨拉说,“还有这条白痴路,直到海边看不到一棵树。我再也受不了了。真没劲,我再也受不了了。”
吕迪低下眼睛,点燃一支烟,没有回答。
“以前还有一棵树,”萨拉继续说,“竖在广场上。他们居然把所有的树枝都砍了下来。在这个地方,显然他们跟树势不两立。”
“不,”吕迪说,“树是被碎石子弄死的,我跟你说过。自从路上铺了碎石子后树就死了。”
“碎石子从来没有弄死过哪棵树,”萨拉说。
“有,”吕迪一本正经地说,“真的。这里不是一个专门种树的地方,这点我是同意你的。种无花果树可以,橄榄树还行,小月桂树也还行,种地中海的小树都可以,但是其他你要的那些树,那可不行了,这个地方太干燥。但这不是谁的错。”
这回萨拉没有回答。雅克正在起床。他进了厨房,喝他的冷咖啡。
“我喝了咖啡就来,”他对吕迪说。
“注意啦,”萨拉继续说,“或许树是被碎石子弄死的,这有可能,但是那样就不应该把碎石子铺到树底下。”
“他们不知道啊。这里的人,就是无知。”
他们待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孩子听着他们。他也对树有了兴趣。
“我看到那个人在他的船里,”吕迪说,“他在洗船,在洗船,正对着酒店的门前。”
萨拉笑了起来。
“我也真的喜欢乘上那艘船去遛遛,”吕迪笑着说,“但不是一个人,跟你们大家。”他又说:“现在也跟这个人算是认识了。昨天晚上他到滚球场来了,就这么一下子跟我们玩了起来。”
“后来呢?你跟他谈起他的船了?”
“那还不至于,”吕迪说,“到底只是刚认识。”
“我,”孩子说,“我跟爸爸和吕迪去游泳。”
“不,”萨拉说,“我还是要说今天早晨你别去。”
“为什么?”吕迪问。
“太热。”
“我要去,”孩子说。
“阳光对孩子有好处,他们也经得起晒,”吕迪说。
“我确实夸张了一点,你要去就去吧,”她对孩子说,“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萨拉对吕迪友情很深,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愿意听。孩子瞧着她不敢相信。
“你要去就去吧,”她又说了一遍。“你们要去都去吧。”
女仆走出屋子。她用力揉眼睛,对吕迪很可爱地问了声好,男人都使她动心,就像对牛奶动心的猫。
“你好,吕迪先生。”
“你好,你们这房子里的人都起得这么晚。”
“热得没法闭上眼睛,那也只好在早晨睡了。”
她走入厨房,也喝起了冷咖啡。雅克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浴室里淋浴。吕迪坐在游廊的台阶上有意盯着河看。萨拉坐在他旁边,抽烟,同时也盯着河看。孩子在花园的草丛里搜索,试图抓住一只壁虎。
“那么,他球玩得好吗?”萨拉问。
“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挺客气。有点儿……冷淡……就是这样,安安静静,但是挺客气。”
女仆出现在厨房窗子前。
“那么,中午吃什么?”
“我不知道,”萨拉说。
“您不知道,那不会是我知道吧。”
“大家去酒店,”雅克从浴室里喊道,“我不在这里吃。”
“那就没必要带了我来度假了,”女仆说。 “他呢?”
她指指孩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