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感
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4月20日至22日这三天。这三天看起来平淡琐碎通俗家常与往日没有任何区别,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因为我的身体而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奇特、突如其来却又挥之不去如水墨画般层层浸染开来的变化。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种风雨欲来黑云压在心头的体会。
当一切都已经过去,当我的内心再一次晴空万里之后,我把那三天的体会叫做预感。曾经一段时间以来,我轻易不愿意去回忆那三天内心的经历,因为每回忆一次,我内心的电闪雷鸣会直接导致我身体的反应——我真的会心悸,会出汗,然后才能慢慢平静下来。但是我现在要把这一切呈现给您,我要把我所有的内心的、身体的体验与您分享,我要刻画生活在那些日子里给一个普通女人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那几天,那些血
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2004年4月20日,我起晚了。因为昨晚我睡得实在太晚。没办法,我要搬家,要收拾东西;而我的丈夫陈卫东是指望不上的,他在电视台工作,是《体育新闻》的制片人,比我还忙,而且说走就得走,所以几乎所有的家务事都要我承担。搬家最艰巨的工作就是装箱,而装箱的工作也实在不能找小时工,因为我要分类,而且我要清楚分类的结果,所以必须亲力亲为。
当我从公司披星戴月地回到家,我看着不大的客厅放着十几个叠着的纸箱子,我告诉自己:今天要把所有的书打包收好,要把散乱的小物件放进“集装箱”,然后跟搬家公司约时间。明天早晨要把玻璃制品,还有小件的家用电器放在车里,自己好抽空运到位于望京的新家去。
环顾客厅,墙上已是光秃秃的,满墙的镜框已经摘下,原来挂着我们全家福照片的地方留下相框的痕迹。我看看台历,盘算着搬家的具体日子。台历是用儿子的照片自制的,此时儿子已经送到我的父母家。
我使劲看着照片上儿子甜甜的笑,大概看了10秒钟也许更长,然后我疲惫的身体就又充满了能量。这样持续、专注地看儿子的照片,于我已是家常便饭。儿子那浅浅的天真无邪的笑容就是我的强心剂我的充电器啊!儿子,我常常想,好儿子,妈妈有了你还怕什么呢?什么都不怕!再累妈妈都能挺过去!妈妈要和爸爸共同努力,为你创造一个好的未来不是吗?我们马上要住进新家了,新家宽敞明亮,可以摆放更多的玩具呢。
我喝口水,打开音响,抖擞精神开始干活。音响里流淌出来的居然是贝多芬的《命运》,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觉得有点儿做作,但是此时此刻,那铿锵的乐蓝正仿佛劳动号子。也罢,我要用《命运》鼓足干劲,力争尽快把活儿干完,我相信音乐是有疗效的。我一边跟着哼唱,一边不停地分类装箱,我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要快!我还有没完没了的事情要做!
究竟几点睡下的我不记得了,总之4月20日的早晨很快到来。我被暖洋洋的太阳叫醒,拉开窗帘,窗外已是草长莺飞,春光明媚。可惜,我没时间享受这温暖的春色,我知道这春色大好可我没有时间,我知道我辜负了这大好春色可我必须辜负。
今天努力工作才能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心无旁骛地完全彻底地享受这春光。我一边这样劝慰自己,一边不舍地走进洗手间,开始洗漱。照镜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瘦了。瘦了好,我想,我不是一直希望瘦么?儿子已经两岁半了,也该瘦了;再说,像驴一样的工作和生活怎么会胖呢?脂肪的不告而别没有让我有一丝不爽,我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励志漫画就在这一刻不容置疑地窜到了我的眼前:那是一头快乐的驴!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对呀,我想,反正已经是一头驴了,那么我为什么不做一头快乐的驴呢?!
我锁上房门下楼,我打开车门,把沉重的文件和材料扔进车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装玻璃器皿的纸箱子放在后座。刚掏出车钥匙,我忽然停住手,我开始疑惑,家门是不是已经锁好?锁了还是没锁?我犹豫不定,终于下车,上楼,推一推门,确定房门已经锁好,才又下楼、上车。我摇摇头,最近总是这样,做过的事,转脸儿就忘。
我起步加油,车窗外的景致在耳边风一般滑过。我顾不上看,我心里迅速盘算:先要去办公室,因为公司明天也要搬家,我必须要安排;然后我要去见个客户,是一家新开张的特色酒楼,要请我们做一套营销推广方案。这些要在今天下午3点30分以前搞定,因为这之后我还要去新家附近参观几个幼儿园,儿子该上幼儿园了;还要给丈夫买条领带,回家的路上要去干洗店把丈夫的那套灰西服取回来,他明天要去上海开会……我一边开车一边盘算着最科学的顺序。多少年以来,我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开始。
突然一个红灯,我紧急刹车。光顾着想事,没注意红绿灯的变化,差点闯红灯。安全,安全第一,不能给自己添乱,不能给警察叔叔添麻烦。我正在告诫自己的时候,一辆120急救车呼啸而过。那一刻,普普通通的那一天,平淡无奇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起了涟漪……
我突然感到伤感,而且那伤感的痕迹清晰可见;当120掠过我的身旁时那伤感变成了无助;看着120飞也似的远去,我心里竟然有些惶恐了。不过心里有了归有了,我还是得该干吗干吗!于是我提前15分钟成功搞定客户!下午4点整到了位于望京的新家。
新家在望京一个闹中取静的不大的小区。小区里很安静,我下车熟悉了一下环境,然后搬着纸箱子上楼。刚装修完的家里空空如也,这里将会被填满,家具、电器、书,还有一家三口的欢笑和幸福。我憧憬着想象着默默规划着,最后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
4月20日下午5点整,我从位于望京的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离开。我已经替儿子报了名,这家幼儿园是易菁推荐给我的。易菁是我公司的合伙人,我们是大学同学,也是好朋友。儿子小名叫嘟嘟。嘟嘟,呵呵,想起儿子我就想笑,小东西一天到晚金箍棒不离手,易菁说他有暴力倾向,该上艺术幼儿园。
本来姥姥、姥爷要求他们带,在姥爷所在的航天部内部幼儿园就读,但是每次回去我都发现:姥姥、姥爷已经管不了他了,主要是舍不得管,所以我下决心不管多忙,也要把儿子带在身边,教育好儿子是首要任务,这是我和丈夫的共识。
刚刚从幼儿园出来,就接到设计师阿酷打来的电话,要我回公司看看下午谈过的那家酒楼的视觉系统设计,客户催得很急,要尽快定,我于是又驱车跻身在北京拥堵的环路上,而晚餐只能靠车上的一包饼干打发。
等我搞定一切拖着疲惫的身体,拎着丈夫的西服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11点半。刚进门电话就响了,我把西服搭在沙发上,跨过客厅满地的纸箱子,冲进卧室。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半了吧,我打了三次都没人接,老公不在家吧。”
是……是……是……很熟悉的声音,但是好久没听到了;电话有点儿回音,是国际长途!我飞快地在脑子里搜索着,终于锁定了一个目标——秦勇教练!秦勇是我上大学时的长跑教练,上个世纪9()年代初出国,到今天已经十几年了。
“秦老师!真的么?你是秦老师么?”
电话那头的笑声已经回答了我:“不能这样啊,秦老师的学生要老公在和不在一个样。”
“陈卫东比我还晚呢,快回来了也。”我看一眼床头柜上的小闹钟,23:31,“算得还挺准的,洛杉矶是早晨吧。”
“什么时候来跟你秦老师见一面?不过你还是别来美国,回头再让人给当成人肉炸弹。”秦教练又说为让他的女儿安妮了解欧洲文化,要利用美国国庆节的时候,带安妮去趟英国;而我的妹妹小缨在英国航空公司工作,我去英国也十分方便。我笑着答应了教练的邀请:“行,谁让9?11的阴影挥之不去呢?”
电话那头传来我异常熟悉的调侃:“您瞧瞧,师生见个面还得到第三国,唉,恐怖主义害死人呢。”挂断电话,我在台历上写下:与秦教练相约7月英国见。然后我顺手打开衣柜的门,准备把衣服收拾好。
4月21日早晨8点10分左右,我准备出门,忽然感到下身不适,于是去卫生间,有血。月经已经完了,怎么又有血?最近,有多久?我忙得不记得了,总之有不算太短的时间了,内分泌紊乱,这都太正常不过。我是女人,但我不是个娇气的女人,这算什么呢?我一边这样安慰我自己,一边穿鞋出门,同时我在努力地克制前一天早上120呼啸而过的那一幕在我的脑海里重现。
公司搬家很顺利,易菁带着大部队随搬家公司的车去了公司新址,我独自留守在杂乱无章的旧办公室里,等着搬家公司回来搬走沙发、坐椅和最后一个装满资料的笨重的铁质文件柜。我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喝着,我想要庆幸搬家工程速战速决,庆幸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成功遏制了120那一幕的重现。
我在沙发上坐下,又站起来,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此时片刻的安宁竟然让我有些坐立不安。我想我应该干点儿什么。干脆,自己动手,试试看能不能把文件柜挪到门口吧。
我去用力地移动文件柜,我低估了它的重量,高估了我的力气,很不巧,或者说很巧,就听“喀”的一声,我把腰扭了,不能动了。
这怎么行?我冷静片刻,拿起放在窗台上的电话,给我认识的按摩专家常叔叔打电话。他让我“保持原来姿势站着别动,半小时后轻轻活动试试”。半小时后果然可以动了,易菁也按时返回。跟易菁交代几句,我去了附近的医院。拍了片子,问题不大,稍微有些错位。我就这样拿着片子直接去了常叔叔的诊所。
我趴在床上,按摩师常叔叔给我复位。他在我腰上按摩的第一下我的感觉却是那里又出血了,而且很多。多到什么程度我当时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一天以来我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那辆呼啸而过的120急救车的声音突然回旋。我的心被什么重重地拉扯了一把,然后这颗心往下沉了沉。
离开常叔叔的诊所,是2004年4月21日下午3点50分,易菁打来电话向我询问腰的情况,我说:“腰还好,就是那里又出血了。”
“你去医院看妇科,现在就去不然我什么都不跟你说!”易菁果断地挂了电话。
我只有就近去了附近一家医院。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医院里显得十分冷清。妇科的大夫有点儿心不在焉,说没什么大事,给我开了点儿治宫颈炎的栓剂和一些消炎药,就打发我走了。
刚从医院出来,就接到妹妹洪小缨的电话。她刚刚随丈夫去了成都工作,所以北京的房子出租了;可是租出去已经快一个月了,房租还是迟迟未付。她让我去看看,催催。
“你居然没收押金就把钥匙给人家了?”
“租房的是个演员,她信誓旦旦的,还给我看了她拍戏的照片,跟好多导演、演员的合影,”小缨有点儿委屈地说,“而且中介也是家大公司。”
我越听越觉得这个租客像个骗子:“一口一个小缨姐姐就把你搞定了是吧?哼!”
“……”洪小缨无言以对。
我一不做二不休,随即打电话给那个所谓的演员,约定时间给钱。她在电话里对我苦苦哀求。果然够嗲,这套还是用来对付男人去吧,对我无效。没什么可商量的,要么给钱,要么搬走。最后她答应:晚上9点在妹妹家等我去拿钱。
晚上9点很快就到了,女演员没有出现,而且手机关机。一小时之后,女演员仍旧没有出现。我感到问题严重,让物业人员给我开门,室内略显凌乱,拖鞋一只在门口,一只在客厅中央;而且,新买的电视机和西门子洗衣机不见了;我给小缨打电话,小缨果然不知道电视机和洗衣机的去向。我立刻换锁并拨打110报警,随后,我拨通了薛涛的电话。薛涛是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是《法制进行》的主编,这事得跟他聊聊。
午夜,悄悄潜回、因为进不去门到物业要钥匙的演员被蹲守的警察逮个正着。“嗲精”要求“跟小冰姐姐单独聊聊”,被我拒绝:“有困难找民警,有什么话跟警察叔叔说。”征求了小缨的意见后我说:“你赶紧走,这房我不租给你了。”
闻讯赶来的薛涛一副很懂政策的样子,“你要看清形势,现在已经不是经济纠纷了,现在是刑事犯罪!你必须尽快把电视机和洗衣机还回来。”
处理完一切,天光已经放亮。“走,我请你吃早点。”我打了个哈欠,对薛涛说。
“拉倒吧,你还是回家睡会儿觉吧,我也得回家睡会儿。”大概看到我掩饰不住的困倦,薛涛拒绝了我的邀请。
“好吧,等小缨回北京我们一起请你吃顿好的。”我也没坚持,我们认识已经20多年了,实在不需要客套。可不是,如果我现在死了,都认识他大半辈子了。
大概凌晨5点钟,我终于躺在了自己家的大床上。天已经微亮,我无法立即入睡。我脸朝天花板瞪着眼睛,我这一天都忙了些什么呢?我一翻身,丈夫的枕巾上还留着他浓重的头发的味道,我想丈夫这个时候肯定还在上海的宾馆里酣睡。也许实在太困了,想着想着我终于睡着了。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坐上一艘船奔向一个小岛,据说儿子的幼儿园就在那个岛上。
我在船上远远地看见儿子玩耍的身影,看见了儿子天使般的笑容,看见儿子虽然很淘气但是很有大哥哥样子地帮助那些小妹妹滑滑梯。
我冲着儿子喊:“嘟嘟!妈妈接你回家了!”儿子看见我高兴地喊:“妈妈!妈妈!”
我要走向儿子可是我脚下波涛汹涌,我的船根本没有靠岸的意思,反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儿子越来越远!我着急了:“嘟嘟!嘟嘟!”我奋不顾身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
突然,我醒了。
我翻身起床,迅速梳洗。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要在今天上午知道:我的身体究竟怎么了?我预感到的究竟是什么?!
我以最快的速度驱车来到北京市妇产医院。这家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名的专科医院,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儿子出生的地方,所以我对它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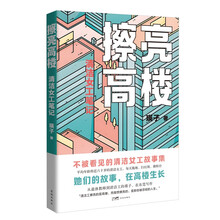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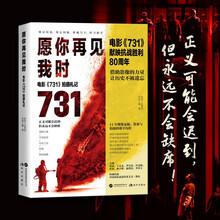






——北京市妇产医院医生 周琦
“子宫”装着一个女人的梦想、一个母亲的光荣,它不管在哪里,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暖意。愿这本《子宫》带给大家如沐春风的温暖。
——北京市妇产医院医生 李凤霜
珍爱生命,拥抱阳光,幸福生活!
——北京市妇产医院护士长 康琳棣
祝天下的女性朋友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北京市妇产医院护士 侯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