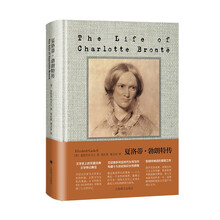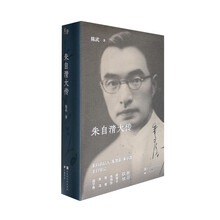1996年,在吉林师范学院召开的一次关于“文学史论”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提出“文学史无法还原历史,文学史也无须还原历史”,这颇引起一番争论。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文学史确实无法还原历史,但文学史应最大程度地还原和认识历史”。于是,我提出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其实,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非同一般的表现,我们似乎很难说他在文学史上失踪了。1918年,他就读于南开学校时就发表过提倡新文化的文章。留学日本,他列名于创造社发起人之一。1925年,他在《语丝》上与“五四”时声名显著的钱玄同进行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次年,他学成回国,指名道姓地批评提倡“作诗如作文”的胡适“把中国诗坛害得断子绝孙”,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与冯乃超、王独清在刚创办的《创造月刊》上,有宣言、有作品地“发难”于诗坛,为人瞩目,引出不少评论,有“创造社三诗人”之称,并留下了当时颇受好评的第一部诗集《旅心》。1931年1月,他到上海加入“左联”,担任《北斗》编委和“创委会”诗歌组负责人。翌年9月,他与杨骚联系一些左翼青年诗人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后又创办了会刊《新诗歌》,他写出著名的发刊词《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创作了第二部诗集《流亡者之歌》。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创办了诗歌刊物《时调》和《五月》。到大西南他仍然坚持抗战诗歌活动,并出版了最后一部诗集《新的旅途》。此外,穆木天自1935年始直至抗战时期,更是以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家身份产生影响的,他是中国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的开拓者。穆木天如上这些文学活动,在当今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塑造了一个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紧随时代前进的作家形象。
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主要是穆木天的诗歌,在我们的研究中更为重视的是前期穆木天的象征派创作,这带来我们认识中的穆木天诗歌创作对于他文学批评的“遮蔽”。在我看来,穆木天的文学批评较之他的诗歌创作更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第一,穆木天作为诗人的三部诗集,即使被称为“象征诗”的前期诗作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也是在他的以“诗”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他1931年后转向左翼诗歌创作更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把他的“转向”称为“理论自赎”的悲剧,就是说他诗歌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后的矛盾状态,只有通过考察他的文学批评观的变化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第二,穆木天文学批评更能体现“五四”新文学开拓者创作、翻译和批评集于一身的特点,而且,他给我们留下了在篇幅和内涵的丰富和深刻上超过他的诗歌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座需要开发的“矿藏”,仅从近些年来引起研究者关注的他的诗论来看,他的文学批评就有着进一步发掘和阐释的必要。第三,我所着眼的主要是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即一方面,他的文学批评是作为置身日本文化环境中的创造社作家发展起来的,与创造社作家相一致,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创造社作家整体状况不同,他留日期间形成了与法国文学更深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独特性是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域外文学取向的整体状况中比照出来的,而且,他1926年就直接以他对法国文学的独到感受和认识为参照展开文学批评,这使他在“无意”中走进了中国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间,形成某种独立价值和意义,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史中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感受和认识,一一其中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他在《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中对“诗”和“写实文学”的阐释,对“五四”后的新文学向审美形态的转化与发展是十分及时而且必要的,触及到中国文学的一些根本性症结,这些症结始终存在于新文学发展中,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第四,在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描述中,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的被“遮蔽”,无疑与我们所占有的全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相关,我们很难从中发现有关《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的直接反响,甚至连穆木天自己在1930年后都对这些文章以及相应的诗歌创作一再作过沉痛的“反省”和“忏悔”,因此,似乎没有必要把他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对新文学发展“进程”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文章拿出来重新掂掂分量;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时至今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极不充分的,认识到“史料”在还原我们所能看到的新文学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还原了这一历史真相的局限,那么,《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被“遮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一个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在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实际状况的认识不断深入过程中重新阐释的问题,而穆木天1931年后对此的自觉否定,更使问题具有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现象形态的“典型性”。
我对穆木天文学批评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认识出发的,同时又是从对法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关系的思考出发的。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在相对隔绝的背景和环境中,依据中西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精神发展要求自然产生的,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有深厚的基础,并在各自的历时性发展中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二者之间在整体上不具有共时性的横向联系。诸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在欧洲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与滥觞了中国文学之根的先秦《诗经》和《楚辞》一样,是在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各自几千年的独立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即使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期汲取并融会了西域宗教文化的唐代诗歌创作,也难以对几乎发生在同时期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学产生任何影响。各自具有独立的生成和发展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在“五四”一代新文化倡导者的视野中真正发生了联系,或者说,在这些从国外留学回来、更关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真正建立起了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各自迥然有別的整体面貌,建立起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整体比较观,这是他们能够发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能够产生并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西文化是由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化概念构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交流需要找到更有助于两者之间交流的通道,发现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发生联系的更为接近的点;陈独秀面向欧洲倡导新文化更多地借鉴的是法国思想启蒙运动,这源于他对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思想文化发展中具有的整体性和“划时代”影响的认识,正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对法国启蒙思想和启蒙文学的选择,打开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联系和交流的通道,賦予了百年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联系的特殊意义。这就是说,陈独秀开启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之缘,在其后的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成为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关系的一条主线,百年中国对中法思想和文化关系的想象和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留学法国的为多,直接受到法国文学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的法国文学翻译始终居于主导位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