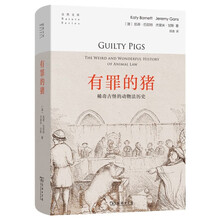至于王雱发议之军器监设置,则又所以重军实精兵械云。其改革学制也,罢明经诸科,改经义论策;并复古制,兴学校,立三舍之法定其等级,行专科之制,各有教授。凡此,皆不尽适合于实用,而群僚亦或予以攻击也。故其变法,尤非王莽之徒重制作,而无规律,如募役新法之办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乃著为令,且又颁其法于天下,是并与秦之变法民莫能议有异。虽然,安石固偏重于法矣,惜未能澈底实行其道,致种其失败之一因,盖既谓“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法者吏也,”而又谓“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则何不使吏必守以法,吏之不良,亦法之所未尽也。安石囿于儒家“徒法不足以自行”之说,亦认为“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于是吕惠卿辈之行新法,适足为旧派“人治”之借口,推翻其所变者。远而大者既未能注意,乃在相位时,复置京城逻卒,察谤时政者,尤失之末矣。然而安石之变法,功虽未成,后世言政者且以安石为戒,而新政之精神则实振往古,惊后世,在中国法制史上固有其光荣地位,与显著成绩。不过从兹以降,直至清末,握政者均以苟安为计,莫敢公然言变,不可谓非受此次失败之影响也。
四日清末变法,毅然兼采西制,使中国之法律开其新端也。清末变法,其思想远承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之鼓吹,其行动爆发于康有为之第一次变法,其结果继续于民国成立,而最后由中国国民党为唯一新法制之创始。但在一次变法以前,清室渐知重视洋务,然当时目的不过羡欧美之船坚炮利,源非根本之图,而旧派则已以奇技淫巧,用夷变夏目之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