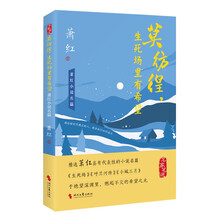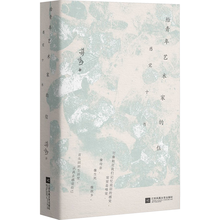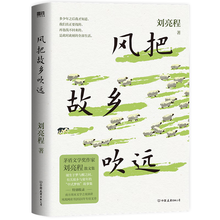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穿越经典》: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断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断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断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杂篇·徐无鬼》)
我要分析的第一则寓言与惠子之死有关。它虽然不是选自内七篇,但因为这则寓言直接与庄子本人有关,是庄子说过的话,所以,我仍然把它当作是庄子的表达案例。
我们知道,惠子是庄子一生最大的论敌,差不多也是唯一的真正默契的朋友。
庄子的一生,不仅穷困、自由和旷达,应该还很寂寞(高处总是不胜’寒呵,我们可以想象他独孤求败世外高手的模样),除了同国的惠子,不见得还有其他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和学生好像也不多,他活着时并无显赫的名声(除了荀子在自己的书中说起过庄子,其他诸子名士都没有提到他)。死后还埋没了很长时间,直至魏晋之间,庄子才声势浩大起来,那时的名人雅士几乎言必称庄子,一部《庄子》则成了玄学家们清淡的灵感源泉,庄子那逍遥闲旷放浪形骸的生存方式,也成了魏晋一代遵循的榜样或风行的时尚。
尽管庄子喜欢和惠子辩论和抬杆,尽管庄子在自己的文章中处处嘲弄惠子讽刺惠子,常常直接或间接、认真或戏谑地“糟蹋”惠子(有人甚至认为,“内七篇”专为驳斥惠子名学而撰)。可实际上,惠子却是庄子的晚年挚友,也是庄子生前能够直接对话的唯一的同时代大家。
惠子死了,庄子当然极难过。有一次路过惠子墓,估计是有人询问了他的心情和感受,就像现在的媒体记者,动不动拿着话筒用愚蠢的问题骚扰人,美其名曰采访:“庄子先生,请谈一谈你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好吗?”
庄子没有说很怀念很悲痛很心碎之类的话,如果这样说,就俗了,就不是大师庄子了。
当一个人悲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是无法用语言直接言说的,哭泣和眼泪同样也不足以表达。世人常常在葬礼中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那多半是哭给别人看的,内心却未必真那么悲痛。君不见丧礼上还常有雇人哭泣的事情吗?眼泪并不一定意味着悲伤,所以我们常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甚或还说“鳄鱼的眼泪”。
魏晋时期倒是有个名人,曾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过内心的深切的悲伤与哀痛。那就是阮籍。阮籍是个有名的孝子,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过世那天,他正在朋友家下棋,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还是把棋下完,回家后,先蒸了一头小猪,喝了很多酒,然后他只大哭了一声,接着就吐出了大口的鲜血!这才是真悲真痛,才真是伤到心伤到肺了。当然,这样的方式不适合世上的一般人,鲜血可不是谁想吐就吐得出来的。
既然语言和眼泪都无法表达悲伤,而庄子那时已经年老体衰,我们总不能指望他用吐血来表达悲痛,况且母亲与朋友毕竟也不一样。这时候我们看到,大师庄子使用的还是他的杀手锏:讲一个寓言。
把庄子当时向身边人讲的寓言译成现代文大意如下:
说有一位泥水匠,滴了一滴白粉在鼻尖,像苍蝇翼般一薄层,叫一个名石的木匠,用斧头削去薄粉,木匠使劲运转斧头,像风一样快,尽它掠过那鼻尖,泥匠像无事似的一动不动,那层薄粉已没有,而鼻尖安然无恙。宋国的王听说了,找去那木匠,说,你功夫那么好,也替我试试?他说,不行,我的对手泥匠已不在,无法再试了。最后庄子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寓言,看看庄子的语言表达吧。不是用树叶或衣袖擦拭,也不用铲子铲或小刀刮,而是用斧头劈白粉!这不是日常的一般的方式而是极致的方式,这不是有想象力,而是想象的极限(后人不可能超越这样的想象了);这种想象的表达的极限,导致的当然是令人震惊的极致效果(这是怎样的鬼斧神工啊),带来的是极度的内涵和寓意:泥匠和石匠无比默契,这两个人相互信任到了世所罕见的地步。
读这个寓言的时候,一般人往往总是惊讶于木匠那斧头功夫的快如闪电妙到毫颠,其实这只是这个寓言的直观表象(庄子的寓言从来不直接说事论理,其寓意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深奥隐晦,不殚精竭虑费尽心血,难窥其真意和深意)。在我看来,这个寓言的另一个人物泥匠即郢人也许更值得我们惊叹和关注:他对木匠的信任,他的纹丝不动的配合,才是劈白粉这一行为或事件的关键所在。也许我们可以在世上找到别的斧头功夫极好的木匠,可你很难再找一个当斧头呼呼生风闪电一样劈向自己时岿然不动的泥匠。只有寓言中的木匠本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当泥匠不在于人世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向别人表演斧头绝活了,即使国王也不行。对木匠而言,泥匠是唯一的不可更替的。就这样,这个极限表达导致了表达的极限:两个人信任到了极点默契到了极点。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就像光线离不开光源,就像硬币的正面离不开反面。
运用这个极限表达的寓言,庄子不仅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悲伤,还道出了终极性的信任与默契,道出了生命之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