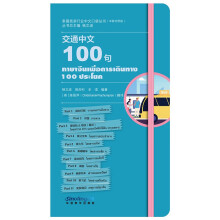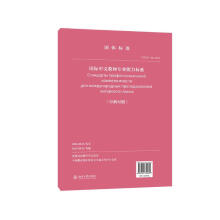但是,传播的实质不仅仅是介绍“我有”,更重要的还在于沟通,达到“你知我有”“你我共有”;而沟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与认同。所以,这样的文化“大礼包”虽看起来内容丰富,价值可观,却难以保证接收者能从中会意真切足实。数据显示,1900-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卢萍、宁霁,2012)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事实表明,这些文化大礼不但没送出去多少,而且打好的“礼包”似乎被接收者束之高阁,没有真正打开来消受享用。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文化犹如矩阵,是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立体系统——它的表层由物质形态构成,体现为对象化劳动的物质成果,如衣食住行、生产生活资料、形态具体的人文环境等。它的中层属于“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雕像的意蕴;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里的人的精神产品,社会理论宗教神话学;人类精神产品的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等”(覃光广等,1988:197)。文化的核心层深藏于内部,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
在文化的三个层次中,物质层面是最活跃的因素,变动不居,交流方便,因而最易被传播,容易为交流双方建立共性基础;弱点是容易流于表面,深刻性不足,传播因子个性不突出,导致传播潜力与持续性不强。而文化的心理层面最为保守,同他者的区别性最强也最深刻,是文化类型化的灵魂,故而最不易于传播;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其传播意义却最大,传播的文化价值最高。许多传播活动难于触及到底层的“灵魂”,从而失去了一部分、也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文化意义。
典籍传播无法让文化“触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汉语经典外传中的语言属性这个核心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传播参与者未能深入挖掘作品中的语言价值。我们知道,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符号,还是文化精髓、价值观念的书写者。“语言因指示世界而存在,世界在语言认识中再存在,语言不仅是世界存在的一个本体,语言甚至就是世界存在的本体。”(蔡龙权,2012)语言本身便与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相对应。洪堡特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洪堡特著、姚小平译,2001: 29)。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实际上是民族思维活动形式的凝结。“”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洪堡特著、姚小平译,1999:72)既然汉语传统文献经典的本质就是语言产品,而且文化的立体内涵就蕴藏在字里行间,对外传介这些作品当然也应该把语言的传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其语言属性理应成为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二 汉语传统文献经典的语言属性及传播意义
汉语传统文献经典本身有着天然的语言属性,即语言产品的经典性、符号性、工具性、高度文学化等属性;在其传播过程中,又产生了语境多重流转与反复适应性、超时空性、社会发源性等突出特征。我们不妨将汉语经典外传具有的语言属性析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
(一)静态的语言属性
静态语言属性所描述的汉语传统文献特征,集中反映在汉语作品经典化的形成条件上,这些条件同时构成了其语言属性的主要构件,代表性成分包括:
1.语言产品的经典性
汉语经典文献最突出的本体特征就是文本的经典性。汉语经典作品往往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故而有的成为文化”元典“;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享有较高的知识权威、艺术权威、学科权威和思想权威;是历代读者和社会群体不可或缺的学习范本、史籍资料;通常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经过历史考验之后沉淀下来,又具有相对固定的普适价值的语言文字作品。汉语成语、语言表现惯用手法(如赋比兴的修辞手段、引经据典的传统)、生动的语言素材等,绝大多数都出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文学名著等传统文献作品中长期固化下来、文化价值较高的语言形式和文字产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