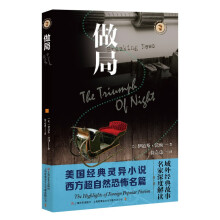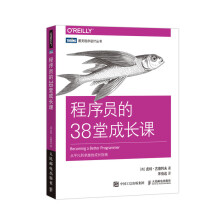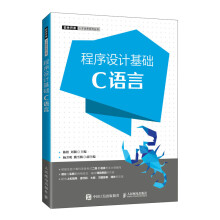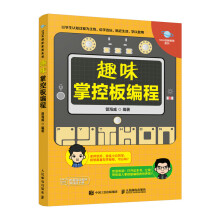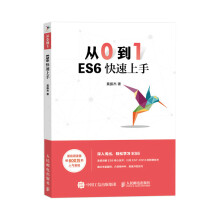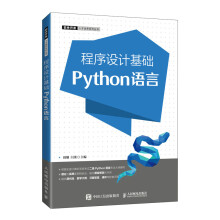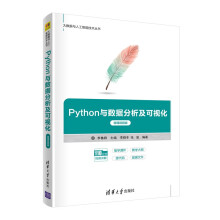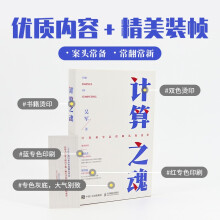代、德之际,国家财政亦不丰给,官本钱的运作却反而有扩张的迹象,《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建中二年(781)五月敕:
宜令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员,……量给俸钱,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须干力什器厅宇等,并计料处分。
所谓“置本收利供厨料”,是否仅指食本,并不确定,因为其他非关厨食;的几项,同样也计利处分。如前所述,公廨本与食本有交替互用的情形,而德宗之目的也止于足用,殊无意于区分各料之用途与所属科目。但由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的建言中,可以看出诸色官本合计之可观数量,其论之曰:
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厨料、什器、建造庭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
……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
俸钱各准品秩给,与息钱无关,息钱用之于干力、厨料等项。唐代置官本钱,皆以诸司大小闲剧或宠异程度而定,并非全然一律。代宗厚与书院、国子监食本,也不过三千贯或万贯,德宗初就拟与待诏官二万贯本钱,手笔之大,令人咋舌。唐政府在税赋不足供费时,仍不惜与诸司高额本钱.应该就是看中其一次置本,生生不息的特色,认为此后国家不需再编制预算,拨款供给各项杂支。毕竟军国之用,名目正大,数量极巨,自不适合用息利法来取给;至于厨料等细目,虽不可缺,却也不足观,何必耗费税赋这样的珍贵资源!
沈既济建言中提及,“当今关辅之大病,皆为百司息钱”。息钱收利,固不仅于供官厨,而供官厨已渐为后期之大宗。沈既济以关辅大病视之,盖官府置本已为在京各司之常制。以代、德之间的几个事例观察,京司食本或诸色本钱似有大幅增加的趋势。然而,本钱出举必须在政局安定下进行,否则利息收不回来,本钱也势必耗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