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们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
20世纪60 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了米尔顿· 弗里德曼,当时他被认为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右翼主义者。大部分人嘲笑他对货币的看法,其“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嘲笑。然而,即使是消费的永久收入假说——这个论证严密的模型说明消费需求取决于家庭的长期预期收入——也受到了毫无道理的批评。
弗里德曼对于公共政策的贡献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述得最为确切,但是由于人们的忽略而被遗忘。因此,我在读博士时未能学习到弗里德曼具有预见性的思想,其中包括实行发放学校代金券、统一个人所得税税率、士兵全部自愿入伍、通过实行负收入所得税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障私有化、实行浮动汇率等政策,也未能学到货币数量增长和平衡预算之间的规则。20 世纪50 年代,弗里德曼提出的思想在当时看来是比较激进的,但是他的许多思想如今已经成为主流政策得以实施,还有一些也已被列入议事日程。例如,士兵全部自愿入伍的措施已经实行了许多年,已得收入抵减税额也成为负收入所得税的一种形式,统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可能会成为国会未来讨论的重要议题,华盛顿地区和其他一些州正在考虑推行学校代金券。
目前对美国社会保障改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个人账户的程度和范围,而不是能否实行私有化。从现在开始,我们可能会遇到与社会保障私有化类似的讨论,即有关毒品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也是弗里德曼最近提出的政策建议之一。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谈及这一问题。
1976 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只是经济学界承认弗里德曼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方面。事实上,20 世纪在政策影响方面,唯有凯恩斯可以与弗里德曼相媲美,但二者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凯恩斯之所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他认为大萧条起因于个人经济的失灵,他主张政府应较多地干预经济;与凯恩斯相反,弗里德曼则认为大萧条是由于政府失灵,特别是货币政策失灵造成的。因此,大萧条并没有使弗里德曼成为大政府的支持者。此外,他还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防止通货紧缩上的失败经历作为支持货币规则的依据。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自由市场和产权保护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弗里德曼无疑成了这场思想较量的获胜者。
想了解弗里德曼思想的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最好读一下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两本著作。他的自传《两个幸运儿》(Two Lucky People)(由他和妻子罗斯合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他从非主流学者转变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个人经历。但是,我认为弗里德曼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其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因为他直接参与了政策制定。事实上,弗里德曼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帮助政府建立收入所得税预扣制度。因此,在他的自传中对学院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即“一定要在政府里工作几年——但仅仅几年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政府工作超过两三年,你就会深陷其中,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看法,我也只在这件事上与他的意见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希望始终在学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学者,在政府工作两三年也很长。
弗里德曼认为向国会论证某项政策有效的做法也是无用的,他曾说过:“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试图向国会论证某项政策的有效性是在浪费时间……花相同的时间写篇文章发表……或发表演说,在影响政策决策方面都要比向国会论证更为有效。”(“发表文章就是有效利用时间”的看法令我很兴奋,因为我是《商业周刊》的长期撰稿人。)在1966~1984 年弗里德曼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稿期间,他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特别大。但是之后为了一些记者的利益,《新闻周刊》终止了他的撰稿工作——这也许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不明智的决定。
弗里德曼没有把在我看来他最好的那张照片收录进自传,我认为这是该自传最大的遗憾。这张照片由芝加哥学派的乔治·斯蒂格勒拍摄,照片上的弗里德曼在驾车去芝加哥湖边游玩时被警察处以超速驾驶罚款,从这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正在真诚地和地方当局合作。
米尔顿和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都是“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人,这个社团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组织。1974 年当我还在芝加哥大学做米尔顿的学术助手时,我收到了来自“朝圣山学社”的邀请函,希望我出席他们在香港举行的会议并发言。毫无疑问,我征求了米尔顿的意见,询问他我是否应该出席会议。出乎意料的是,他认为这个组织应该停止活动。他解释说,二战以后这个组织在促进小国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思想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认为1974年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进行,因此这个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此外,他觉得此类组织有永久存在的倾向,即使它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也不会自动解散。他甚至认为“朝圣山学社”应该主动宣布该组织已经达到既定的宗旨,然后自行解散。
遗憾的是,我听从了米尔顿的建议,回绝了对方的邀请,没有出席香港的会议。因此,多年来我都没能与出席“朝圣山学社”会议中的其他杰出思想家进行交流。直到1992 年,我第一次参加了该组织的会议,才得以和这些思想家相互切磋。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众多左翼经济学家和记者们的嘲讽,弗里德曼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和自信心。多年前攻击他的那些人,现在也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借用他对凯恩斯的著名评论——“现在我们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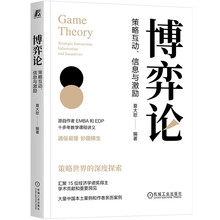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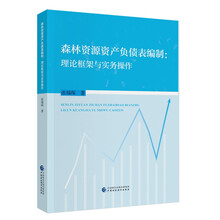




——加里·贝克尔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反常识经济学》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