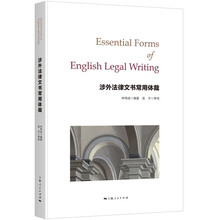申言之,通过违法性概念的引入,并强调狭义“侵权”类型的优先适用性以及“违法”侵权、“背俗”侵权的严格受限性,既维护了私法自治,又克服了因此而导致的缺陷。因为完全的私法自治意味所要求的私法自足性,换句话说就是私法的封闭性,而这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因为纯粹的私法自治从未作为一种事实实存于现代社会,因为公法和私法作为一对矛盾,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既有对立即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也有二者统一即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的一面;且私法与自由具有天然的联系性,而不加任何的限制的自由必定会走向自由的反面,从而也有必要引进公法规范对其加以限制。例如,若坚持绝对的私法自治从而坚持绝对的意思自治,则当事人间可能会通过“自由的”意思而将自己出卖给他人当奴隶,甚至“出卖”自己的生命,而这显然既背离了私法精神的本质,又违背了公法秩序。
在明确了违法性对于维护私法自治的意义后,我们必须要对违法性所涉及的“法”的外延加以分析。私法自治要求这里所说的“法”首先应是民法所规定的法律规范,从权利人的角度看,这里所说的“法”指的是授权性规范,权利人享有一项绝对权,就意味着义务人负有消极的不侵害他人权利的义务,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就意味着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不得侵害他人的义务,从而具有违法性。可见,权利侵害与违法性是密不可分的,“只有那些使用‘权利侵害’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才需要违法性这个概念”①。最初,权利侵害对应的是直接侵权行为(积极作为的侵权行为),这是与传统的关于违法性理论的通说——“结果不法说”相吻合。但对于既不能根据特殊侵权提出请求,又不能依据传统的一般的直接侵害行为解决的中间形态的侵权类型,德国判例学说创造了安全保障义务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权利侵害与作为义务间有了紧密的连接,从而权利侵害与间接侵害行为(不作为)间也获得了某种对应关系。总之,与违法性相关的民法上的“法”仅指确认“权利”或义务的规范,并非所有的民法规范都可成为这里的“法”而被违反。具体说来,首先,侵权法作为保护“权利”而非确认权利的规范,其本身不属于这里的“法”的范畴,那种想当然地将侵权法规范作为法定权利或义务来源的观点显然是欠妥当的。其次,任意性规范多与合同法相关,且其本身就不存在违反与否的问题,因而不应包括在这里的“法”的范围之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