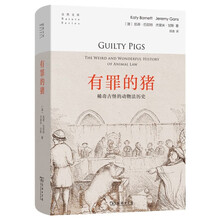第一,葛兰西的“法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强调国家和法的暴力镇压职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学者认为国家和法的职能不仅仅限于镇压与强制,还包括“同意”,法是创建社会同意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观点由葛兰西首创,并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之中。根据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是单纯地通过国家机器的武力强制所获得的,而是通过依靠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意”而获得的。市民社会不再被认为是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的领域,而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体等舆论机构所组成的意识形态领域。上层建筑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政治社会的领导权通过强制来实现,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通过教育来争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来实现。而法律成为国家对每个人不断进行教育、使人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步调一致的工具。葛兰西指出,资产阶级的法律观与先前保守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观相比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资产阶级把自身看做处于不断变动中的有机体,能够吸引整个社会,使之被同化而达到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国家的职能已经在总体上发生了改变,国家已经变成了“教育者”。①
阿尔都塞在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把国家机器分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领域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普兰查斯根据结构主义理论提出了法是社会各种力量黏合剂的论断,进一步发展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关于法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二,哈贝马斯的“法的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实行“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但其仍然还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合法性的危机,而树立合法性又以建立“信任”为基础。他指出:“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①信任的实现是通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完成的。
法律同样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把法律定位于“事实与有效性之间”,并揭示了法律的纯粹事实性和法律对合法性要求之间的张力。法律的事实性在于,法律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和强制的手段。但是法律仅仅凭借其强制力迫使人服从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使人们自愿地服从法律。这就要求法律具有合法性。“由于国家权力媒介是用法律形式建构起来的,因此,政治秩序依靠的主要是法律的合法性要求。也就是说,法律不仅仅要求得到接受,或者说,法律不仅要求得到实际承认,而且要求值得承认。”②
法律的合法性来源于哈贝马斯交往活动理论,没有体现交往活动中的分散形式的人民主权,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法律。为了解决法的事实性与法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问题,实现法的合法性,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他说:“一种法律秩序之为合法的程度,确实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其公民的私人自主和政治公民自主这两种同源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也是归功于交往的形式——只有通过这种形式,这两种自主才得以表达和捍卫。这是一种程序主义法律观的关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