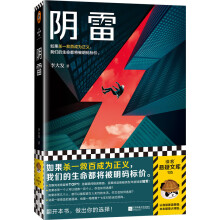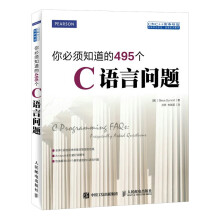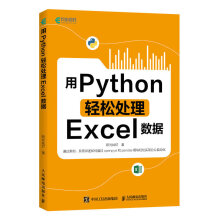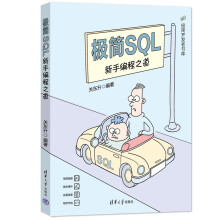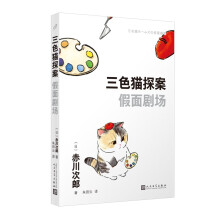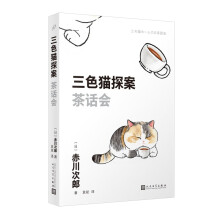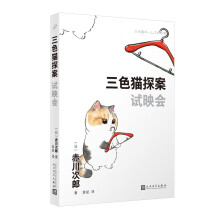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中年以后,他的体力支持不了,便把主要的采矿和种地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大儿子刘勉斋和二儿子刘福安,他自己每天赶着一头黄牛驮运铁矿到桥板沟、连界场铁厂里交称。”厂矿是个小社会,威远的厂矿也是哥老会活跃之所。光绪二十年(1894)时,川省矿务尚未兴起,川督刘秉璋便曾结合前任丁宝桢的“教训”奏道:“川省众所指称矿产多在番夷境内,且自兵灾后,腹地伏莽未净,会匪、咽匪时虞窃发。前督臣丁宝桢于光绪九、十两年(1883、1884)间试办矿务,不独无利可取,且几外酿边衅,内炽匪氛,旋即停止。”民族及“边衅”问题姑且不论,矿场与秘密社会的关联确是灼见。具体到清末威远的情况,亦为刘秉璋所言中。刘香亭因家贫而采矿,由采矿、送矿而在“袍哥码头”加入哥老会,既表征了哥老会借着乡土社会的人员流动而铺展网络,也说明了矿业对威远农村社会的影响。哥老会桥板沟码头有大仁会、大义会、大礼会、大智会四个“堂口”,刘香亭是大义会堂口的“舵把子”。作为义字堂口的掌舵,刘香亭有相当的号召力,“当地大都知道刘香亭常自豪地说:‘我随便到哪里,只要喊一声恭喜发财,叶子烟就有四十八皮,可以摆个小小的烟摊子。’”
据笔者所见材料,没有对清末威远团保组织结构的可靠记载。结合此次案件反映的情况及采访材料,大体情况是每场设一保总,其下依次为保长、团首和甲长。刘香亭被公举担任甲长多年。周善道根据采访所得的一段总结很能反映民举官任的甲长刘香亭的角色:“清王朝设保甲,一面为的是防止人民反抗,一面为的是便利征收税款,但人民对团首、甲长中一些人的希望,是在消极方面也要有应付官府的绐、骗、推、拖的能力和办法。这本是一个矛盾。若果有人站在群众的立场,对群众的利益能够担当担子,甚至于坐牢杀头都担当下来,那是人民最爱戴的自己的首事人了。刘香亭作甲长,正是平时在一些事实中,经过群众考验,由人民公举出来的。”刘信临去世时,刘香亭已经二十四岁了,他是否曾从祖父那里习得团保系统基层领袖为人处世的一招半式,我们不得而知却是可以想象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