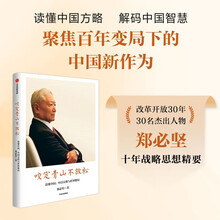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进士出身。20岁(1878年)时因偶然机会游香港,得见“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2〕,这是他最早对西方文明的直觉感受,留有良好印象。在此之前(17岁),他读过魏源、徐继畲的著作,知道中国以外尚有西方列国,但没有深入的领悟。
此后康有为搜读可得西书,他自己提及的有林乐知所编《西国近事汇编》、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傅兰雅的《佐治刍言》等书。苏俄学者齐赫文斯基(ScrgeiL.Tikhvinsky)说康有为颇受《佐治刍言》的影响。萧公权同意其说,认为康有为的西方知识得自《佐》书不少,甚至于说康氏《大同书》中的“公议院”一词即可能得自《佐》书(3)。传教士中除了林乐知、傅兰雅之外,李提摩太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不小。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举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康有为〕几尽归纳为结晶,若特异之小指南针焉。”(4)
康有为在1884-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大谈清廷改革之道,其中关于召开议院者,有第一、第二、第四各次,如果加上他为内阁学士濶普通武所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共四次之多。此四次上书,先是说开国会于皇家有利:“皇帝高坐法官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继则说:有国会则“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第三次仍采前人说法,谓国会“以通下情”于政治发展为大利。为潤普通武所草的奏折,则从三世之义去说理,谓“春秋大义,扰乱之后,进以升平”,中国当“上师尧舜三代,外釆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可见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劝促皇帝召开国会之意,既明显而又积极。
但康自第五书起即不再提国会之当否召开,急转大谈开制度局。制度局是一个决策机构,只要“妙选天下通才二十人,以王大臣任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新制新政,斟酌其宜,……考覆至当,然后施行”。制度局之下有十二局,为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显然康已将制度局取代原先所拟的国会,十二局为执行机构。他似乎已感到开国会缓不济急,只有制度局可以立竿见影,依靠皇权来改造中国。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转变?此应有两个答案:第一,立开国会与康之三世之义说相矛盾;第二,康有为是个寡头主义者。康有为在儒家思想中建立了一套“三世之义”的理论,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无君,无法律,无礼仪;进入升平世之后,订法律,严礼仪,是小康的局面;太平世则为大同世,《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是写照。康有为说大同世为“公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公政府只有议员而无行政官,甚至于无议长,诸事从多数决。他指的就是议会政治的理想,此一观念在阅读西洋典籍时得到,加以诠释发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