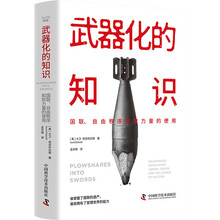中国的“制度文明”
曾经研究共产党选贤任能实践的学者潘维提供了一个区分东西方治理方式的框架。①潘维提出,所有人类事务的治理都涉及以下四种因素:执法(法治)、问责、责任以及道义。“由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他主张,“中国的治理更多依赖于道义和责任而不是执法和问责。”
欧洲社会拥有明确和稳定的政治分权,而潘维提出“在公元前4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中国,找到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的”。因为那2000年的中国社会就像“一堆散沙”,由许多独立的、小规模但大小基本相同的家庭农场组成。潘维认为,这种缺少社会分层的大量农民产生了整体概念上的“大家庭”,尽管存在贫富差距,但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富不过三代”,这意味着社会总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
纵观各个王朝,主要的反叛基本都是反抗当朝统治者的“农民起义”,而不是阶级斗争或者穷人对抗富人,国家也在这以后恢复到原来的社会系统上来。
潘维称,这一事实大致勾画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演变。与个体问、阶级问的律法式的“社会契约”不同,一种小农社会的互相扶持的“道义经济”占据了首要地位。潘维说:“立法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核心问题。”进一步地,由于社会的整体性观念,治理的合法性是和全社会勾连在一起的,而非局部利益或某些党派的利益。“政党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私自利。”
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制度文明”或者民本政体作为一种理念而诞生,随之而来的是为了“家国福祉”而奋斗的道义政府,有道德、有才能的公务员遵循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义务而兢兢业业地工作。“民本”意味着“以人民为根基”。
根据潘维的说法,民本政体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就开始建立,并在几个世纪后由孔子详细阐述。这是延续1700年的科举制度的根基,直到20世纪初。如同任何一种制度一样,金钱交易和裙带关系玷污了这个理想体系,但科举考试和选贤任能的原则是中国“制度文明”的根本特点。
“中国政体与选举式民主制的差异在于选贤任能。择优录用的原则是中国历代治理的核心特点,就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选举式民主制中的地位一样。”当我们和潘维在北京见面时,他如是说。据潘维说,从秦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治理道德体系的其他关键方面是对整个社会的“大一统”观念,这已经深深嵌入了秦朝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另一个特点是纠错机制,监察机构通过“分工制衡”来应对统一的治国集团,而非“分权制衡”。
这些特征在今日的中国十分明显。自毛泽东不同寻常的“阶级斗争”思想被邓小平的现代化建设所取代后,今天的共产党声称代表“全体社会”并且寻求“和谐”。多党竞争缺乏合法性,因而被否定。理由是,这可能会导致以“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的名义分裂“大一统”。
再从理想转到现实层面,中国和其他被孔子影响的政治体制都存在“纠错”的监察机制。通过独立的审查委员会,新加坡已经在治理中有效地根除了腐败。这样的纪律机制在中国同样存在,但它的有效性取决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意愿。
微博的广泛运用是普通人监督和质疑政府的一种方式,也有申诉政府滥用职权的正式渠道,但这种方法经常导致虐待和威胁。中国事实上的联邦制度设立了一个各省和中央互相制衡的体系。视具体事务而定,四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三级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发挥切实的影响。最后,正如潘维看到的,党和国家之间存在分权制衡,尽管不是短兵相接。他将此与苏联做了区分,苏联这个国家是为政党而设的——“政党国家”——而中国则是“国家政党”,党为国家输送人才。这是儒家传统的回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