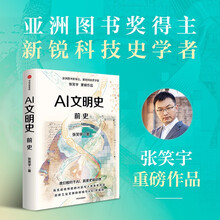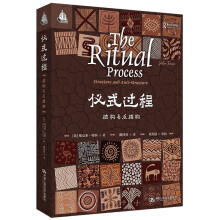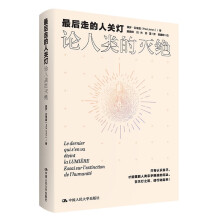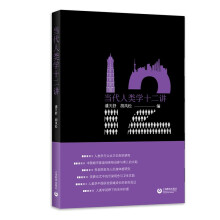国族与世界体系<br> 人类学家或惯于使用文化概念,或惯于使用社会概念,两个“流派”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矛盾的。“文化的”人类学家说,在他们的概念体系里没有“社会”一词的位子,他们研究的“文化”,属于一地、一族共享的价值与道德体系;“社会的”人类学家则说,文化这个词太抽象以至轻浮,因内容空洞,而难以表达人类学家研究的那些可观察、可把握的具体事项,若说还能派什么用场,那充其量就是可用来表示“社会实在”的“表层”一“社会形式”。(1)不过,在两种人类学家眼里,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共同认可的。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应是可数的,不存在惟一的社会、惟一的文化,而这个可数的社会、可数的文化必然有范围限度。一个社会所指的东西,相对明确,任何一个不同层级的人群单位,都可谓是一个社会;但一个文化却不见得有此清晰的单位感,那么它所指的,便一般被等同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人群脑子里的那套观念体系了。人类学家常辩解说,他们未曾认为社会与文化是两相对应的。但他们的研究却表明,无论是将社会视作文化的实质,还是将文化视作群体生活的集体内涵,都是在将文化与社会对应起来。<br> 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家不再如启蒙思想家那样将国族的好未来视作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的使命,而反倒是对于这种在这个世纪到来之后不久便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因素…一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些因素往往内在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或文化——心存深重的疑虑,但他们对“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的论述,却无一不是在重复着国族的历史。<br> 国族概念的谱系学表明,历史上惟一将社会与文化对应看待的时代,就是开始于18世纪欧洲的国族时代②,这种认为一个人群、一个社会必然和必须有其共同文化的观点,历史并不久远。而国族概念之荒诞,又恰好完全与社会和文化概念之荒诞一致。缘起于近代的国族主义,若是一个历史必然,那它与工业社会超越“面对面社会”(即所谓“社区”)的必要性是相关的。<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