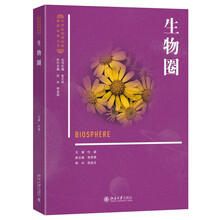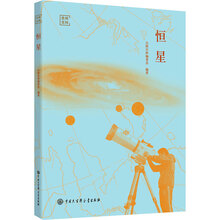斯莱让克料想反对者也许会认为,既然流行的某些评价标准首先必须要装进程序里,那么依靠情境或文化相对性的问题只不过被转移或推迟了。斯莱让克承认,把流行的评价标准即规范归并到科学发现程序中是明显的事实。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是否因此可以认为这些AI程序归并了当下的(local)社会学标准。
一方面,斯莱让克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细节考察程序,并证明解题启发式可以视为体现了直接与社会情境的某些特征密切联系的因素。
但另一方面,他立刻用一个明显的事实表明上述策略的徒劳无益。他例举一个明显的事实:宽广范围的经典科学定律被同一个程序重新发现。这个现象说明,该程序的纯形式化的启发式体现着非常一般性的解题技术。也说明,这些发现应该具有某些共性,而这种共性更可能是人类认知普遍具有的理性原理,而非不同时代具有的特殊的、当下的社会现象——比如,波义耳所处的时代流行的社会现象。
应当说,斯莱让克这个“可能的卫护”做得相当漂亮,击中了强纲领的先天缺陷。的确,如果强纲领认为,社会因素是理论真实内容的有因果效用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情境导致了,不同时代科学家所发现的经典定律具有不一样的内容。那么它现在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理论内容的定律被同一个程序重新发现的事实?这个问题比科学史上的“同一发现”更难回答。SSK可以将同一发现及优先权之争解释为,这正说明不同社会情境下,对同样的科学行动给予了不同的社会指定和承认。可是SSK却无法正面回答机器发现问题。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在所有对斯莱让克的拒斥的反对意见中,几乎没有人谈及这个“卫护”。只有福勒考虑了斯莱让克这个经验检验的适当性,提出了做这样的检验可能会有的,相当复杂的关于不同文化之间如何达成一致,以及如何保持各自独立性的问题。
这场争论是众多对SSK的批评之一,但它发生的视角不同以往。它关注科学发现这个主题,以当时AI研究的新进展为背景,如斯莱让克所说的,BACON等机器发现程序是他用来反对强纲领的“媒介”。
没有“偏激”就没有“争论”,这场争论的“两极”就是心智主义的科学发现观和社会学主义的科学发现观。两种极端观点激烈碰撞后,给我们留下几方面值得思考的问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