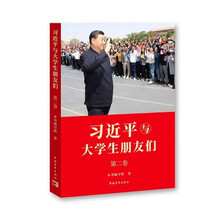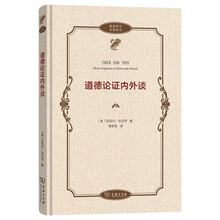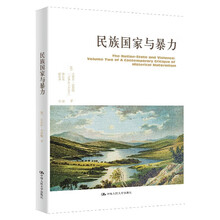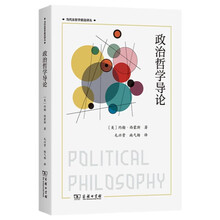今人似已渐渐明白,能够把这种“利”与“善”恒久衔接在一起的,惟宪政耳。宪政经济学有“一切政府都是利维坦”的工具性预设,这决定了它也必有“从道不从君”的风骨。但这里的“道”境界不算太高,只是国家据以存在的一些“游戏规则”而已,它高于私利但又源于私利,无须借助任何超然的价值资源,不必挂起维护“自然正义”的招牌,不必挟某种神祇或历史使命而自恃。因为遵守这种规则的国家,并不是独立于个人价值而存在的实体,它没有自己的行动,不追求自己的目标;它不能脱离个人的义利动机而去定义“社会福利”(或作为其变态表现的“综合国力”),因为这种东西纯属子虚乌有。布坎南在《规则的理由》中曾提到埃尔斯特的《尤利西斯和塞壬》,他把书名中所包含的那个寓言,视为“对未来选择做出先期限制”的经典故事。这个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乍看上去类似于我们的“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希腊版,其大意是,大英雄尤利西斯知道自己意志薄弱,他在驾船接近栖居着女妖塞壬的海岸时,唯恐自己经不住她们迷人歌喉的诱惑,便要求同伴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又嘱咐同伴们用蜡封住耳朵。这是一种为防范未来灾难而做出的决定:若想返回家园,他必须给自己危险的审美欲望预先设防。我们若把这个故事理解为类同于儒家的禁欲说,与张之洞的制情欲如“降龙伏虎”旨趣同,也未尚不可。不过我宁愿像布坎南那样,对它做另一种解释:尤利西斯这种系自身于船桅之上的举动,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宪政主义的智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