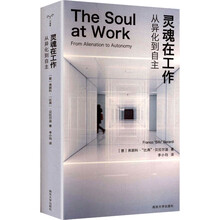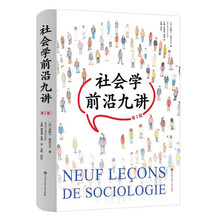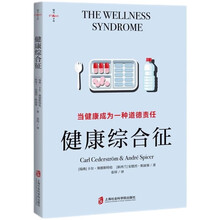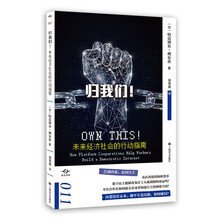由于面对自然灾害和民族灾难时,仅仅是个体的存活和抗争并不能摆脱自身的生命危机,而类的存活和抗争却有可能使所有人脱离生存危机,所以个体生命这时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存活。这是由个体生命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软弱、渺小之现实所决定的。虽然人类的类存在和群体存在在自然界面前永远脱离不了孱弱的地位,但人类作为整体来改善这种地位,却已经由人类的现代化历史发展证明是可能的。《圣经》中“诺亚造方舟”保全全家性命和一公一母小动物,不仅在于告诉我们诺亚一人并不能真正存活的道理,而且在于告诉我们人类存活也离不开动物存活的道理。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就是人类群体因此而繁殖的代言,亲人与他人在此并不存在严格的界线,亲人的衍生才构成了人类大家庭并使得个体生存得到可能。而动物的生存也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动物的灭绝意味着人类作为动物的殊类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礼记·坊记》中的“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这种观念,虽然存在着轻视个体权利和个体生命的问题,但这不意味着“先人后己”在特定时空中不具有对个体至上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意义,即:自然灾害下每个个体如果都能“先人后己”,体现自己对世界的责任,人类的“群体力量”就能够得到体现,并最终展现出与自然灾害相抗衡的力量。
由此,面对自然性灾害,所有的人类生命都是应该珍视的,这成为个体对群体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扩展性理解。一方面,在发生人类危难和群体危难的时空中,所有的生命都是等值的意识,将消解此生命重于他生命的身份贵贱、远近之分,从而使得个体对生命的责任意识处在“抢救一切生命”的奉献状态之中。另一方面,“避免生命的危难”也同样是中国个体对国家机制和职能部门的监督责任。这种监督之所以可以上升到现代中国生态文明示范的高度来对待,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首先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为前提的,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以将个体生命服从于“仁义”和“革命”的规范从而在现实中随时可以牺牲之为前提的。
其次,中国当代个体对自我的责任是中国个体责任教育能否实现现代转化的关键,也是中国个体能否从“依赖责怪社会”的怪圈中突围出来而具有现代独立素质的关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