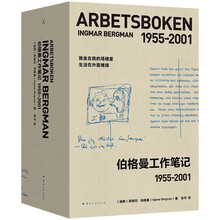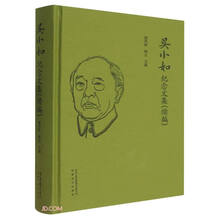岳父见我不期而至,而且送来了这部书,果然喜不自胜。他一个劲地问:哪里借来的?怎么借到的?还如数家珍地为我介绍了有关《资治通鉴》的版本知识。后来岳父曾多次提起此事,并回忆说:“我一下子像贫儿暴富似的,欢喜得不知其所以。”可见能借到《资治通鉴》,当时对他来说确实是件难以忘怀的事。
《资治通鉴》和《苏东坡集》等,都是岳父早年就读过的,但在那时却显得那么珍贵。他不敢大口吞食,舍不得一口气读完。为了尽量延长阅读的时间,他采用了细嚼慢咽的品读法,有意识地控制阅读速度,对每天的阅读量作了大致匡算和分配,一天限读一段,不随意超量。他甚至把小时候祖父教他们读四书五经的带读法(即在第二天上新课前必须把第一天读的内容背出,第三天上新课前又必须把前一天或前两天读的内容背出,以此类推。这种以旧课带出新课的教学方法,叫带读法)也用上了,一天读一段,读上三五天后,再用一天时间把已读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遍。这样,每隔三五天就能增出一天的阅读时间,等全书读完时,不知增出了多少天的阅读时间,同时也不知把这本书读了多少遍。读完一册调一册,全部读完后再从头读起,循环往复,又不知读了多少遍。也真亏得这些书,陪伴岳父度过了在农村的最后几年时光,使他精神上的饥渴和痛苦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粉碎“四人帮”后,借书的路子逐渐多起来了,借书也变得容易些。教育局开始为农村中学每年配一点图书,我所在的学校有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尽管图书数量很少,品种也极其有限,但总算能借到一点书了。我记得,曾为岳父借过一部新出版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岳父读后发现有许多校勘错误。他一条一条地抄录下来,一条一条地加以订正,足足有二三十页稿纸。誊清后,寄给了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结果毫无反应。那几年里,岳父还用从《参考消息》上获得的素材,写过一个讽刺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寄给了复刊不久的《电影文学》杂志,当然也是石沉大海。岳父写文章没有留底稿的习惯,这个电影文学剧也是如此。我想,它大概早在寄到杂志社时就被处理掉了,再无重见天日的可能。
岳父重返工作岗位后,闹书荒的岁月终于结束。在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写作,也不停地读书。最近两三年,由于身体原因,用于写作的时间逐渐减少,而用于读书的时间却日益增多。特别是去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问都用在读书上,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手不释卷。《鲁迅全集》是岳父每年至少读一遍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是他案头的常见书。前两年,他还专门花时间读了《卢森堡集》。岳父有个习惯,朋友们赠阅的新作,都是收到后就一口气读完,不像有的人那样,随手一扔而置之高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