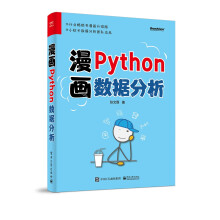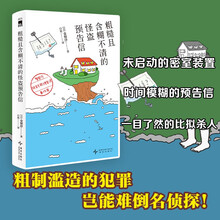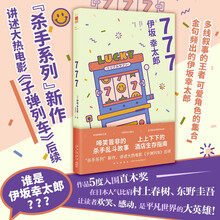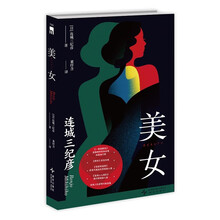对于传统儒学,熊氏上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下弃孔门后学七十子和孟荀八派,只尊“孔圣”,于孔子又以“五十学《易》为界”,只肯定其“创明大道”的后半生。他从心性论角度来阐释《周易》,肯定《周易》、《礼运》所浸透的那种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大同”理想,赞扬《周易》生化不息、雄浑劲健的本体观。②他并不以传统文化为至善至美,“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③,不能成为人们征服自然的有力武器。他欣赏并提倡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以支持现实的个人的尊严,但他亦觉察到宋明诸老先生“他们虽复不忘经世致用率以养成固陋偷敝的士习,因为他们把主静造成普遍的学风,其流弊必至萎靡不振,这个是不期然而然的”④。他认为“人当利用本心之明,向事物上发展,不可信赖心的神灵,以为物来即通”⑨,表明了开掘主观能动性的态度。可以说,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继承了宋明理学的“心性”力量,但突破了其禁欲主静的概念框架,表现了对一种活跃的生命力量的追求,这是他的超越之处,亦是他接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的结果。<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