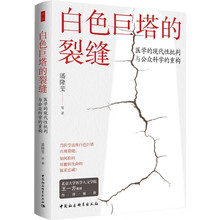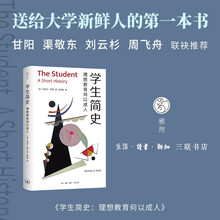第一个方面,社会史研究如何与史学界对话?如何介入其他领域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社会史研究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许多主题上进行了前所未有或少有的研究,但与主流的断代史或传统的专门领域交流还是很少,人们往往只是从主题的分类上判断是否为社会史,甚至无论社会史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时段在哪里,便基本上认定他为社会史研究者,而非该时段历史的研究者。这样一种截然的区分,说明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一个明晰的界限,或者有某种明确的定义,认为研究什么的或怎样研究的就是断代史研究者,否则便可以归入他类。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太多见,比如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学者多以研究中世纪的欧洲著称,但人们不会说:“哦,某某不是中世纪史专家,他是研究社会史的!”
这种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史研究以外的人们。社会史研究者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我们不只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不把我们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隔绝开来,而能与其分享我们的研究视角、方法、材料和见识,那会是什么状态?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学习社会史,首先应该学习史学史。想想国内较早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之前不是研究政治史的,就是研究经济史的。譬如冯尔康以研究雍正皇帝知名,华南的社会史学者多研究经济史。法国年鉴派的创始人布洛赫研究马丁·路德和拉伯雷,这是中世纪史的传统主题,而且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所不屑的人物研究,后来他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探讨王权强化的社会基础,也是一个政治史的主题。孔飞力的《叫魂》以一种“迷信”或者巫术观念为切入点,到最后的王朝权力体系的探讨,总体上没有超过布洛赫这本书。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
选择区域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史研究者往往会遭遇这样的窘境,即无论你如何解释,别的领域的研究者也不觉得研究这样的“小社会”有何必要。我们除了认为这可使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细之外,也无法说出更多的道理。这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区域性的研究旨归局限在了“本地域”,而不是讨论超越这个“本地域”的大问题。以往已有学者提到“跨区域”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使自己的研究空间扩大,因为任何区域对于下一级区域来说都是“跨区域”的,而是要使自己的问题“跨区域”,无论研究的是明代倭寇还是卫所制度,无论研究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事件还是乾隆皇帝这样的人物。这样,社会史研究才能走出周氏洪武年间登人黄册的户名,直到康熙年间依然在被周氏后人沿用。从族谱的记述来看,在闻喜县,这类明初户名固定化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当地许多族姓明初定立的户名曾经沿用至明末或是清初,甚或是有清一代结束。
对于闻喜县的里甲体系来说,明初户名固定化的意义在于它使“户”及里甲的内涵均发生深刻转变。由于明初户名长期承传,当年立户入籍的单个家庭,数代之后一般已经衍生为多个家庭,即所谓“历数传而户族繁衍”,①“户”的规模因此得以不断扩展。此外,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赋役改以丁、地课征,“户”由以往的计税单位转变为征税环节上的登记缴纳单位,它在赋役体系中的地位与功用发生改变。②所以,时至万历年间,闻喜县里甲组织中的“户”已经基本衍变为一个承担一定税额的血缘群体。因应“户”的这些变化,闻喜县里甲组织的内涵同样出现较大异动。户名不变与民众迁居之间存在的冲突,使闻喜县里甲体系旧有的地缘格局难以维系,里甲催征陷入了“盖簿皆老名,少现在之人,四徙而居,寻访不易”的窘境。③与此同时,里甲破败、户众繁衍以及合籍、附户等因素的交织,使一户独占一甲或者数户朋占一甲的情况成为可能。所以,自明中叶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倚重血缘关系的倾向越来越鲜明。一条鞭法在闻喜县推行后,该县钱粮悉令各户分限自行封纳,里甲组织在赋役征派方面的功用也较以往有所弱化,而“户”的重要性却因此大为提升。闻喜县钱粮“合户催征”的举措大致就诞生于这种“户”与里甲内涵均发生转变的情境。此一举措不仅认可了二者的转变,而且赋予它们制度化的可能。
我们看到,万历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基本是以“户”为中心来进行。在明末清初闻喜县里甲变动较为频繁的这段时期,当地户大丁众的人户大抵都曾有过析分、统合的变革经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