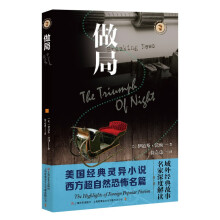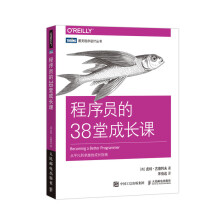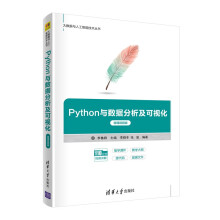听到卞公孝萱先生的西行消息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年初还先后收到他两次来信,数月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他的声音还是相当洪亮,不料竟于9月5日遽归道山。不仅朋友们感到突然,就是他的子女、弟子也同样感到突然,因为他的西行确实太匆忙了。他这一走,不仅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而且对文献会来说更是一大损失,我相信全体文献会会员将会永远怀念这位对文献会作出很大贡献的学术界长者——我们的老会员。
近十多年来,卞公一直称自己是文献会老会员,并且称呼得非常亲切。他确实是一位老会员,还在1980年,我会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学术年会时,他已经参加,并被增补为理事。我们之间虽然也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特别是散会后,由于当时陆路交通很不方便,于是我们一道乘长江轮顺流而下。当时卞公任教于扬州师院,需在镇江下船,而我则要到上海再转乘火车。同船而行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徐鹏先生和华东师大的贺卓君先生等。乘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谈的机会。船到镇江时,已是深夜两点,我一直送他上岸,两人还是依依不舍,这就为后来我们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建立了基础。也就在这近十多年中,我们之间的学术交往逐渐频繁起来。我们研究领域虽然不同,他是古典文学,我是史学,但是相互讨论、互相请托竟然多起来了,特别是他晚年重点在家谱研究,这无形中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也促进了我们之间友谊的发展。记得在2003年12月10日,应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程章灿所长邀请,我去为该所相关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作“读书与治学”的学术讲座,晚上宴请时,由于程所长,特别是徐有富教授知道我与卞公是老朋友,故还特地邀请卞公来作陪。老友见面,分外高兴,有谈不完的话语,从学会中老朋友的近况,到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乃至社会上、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奇谈怪论等。从晚宴开始,一直谈到结束,大家兴致都很高,这是一次难忘的晚宴。就在第二年,卞公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我受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委托,将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内容加以增补,将三卷本扩充为五卷本,重点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70部。那几年我的精力主要都花在这个上面,因为选请每部名著的评介者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