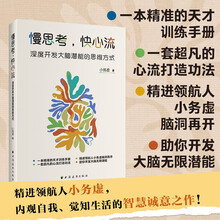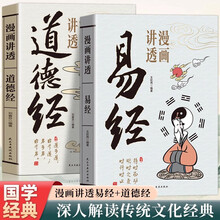例子一:“这是一个三角形”这个原始句。当有人指着一个图形告诉你说它是一个三角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为什么老师能够以话语的方式把一个真实的也即可理解的三角形交付给学生呢?
例子二:“这是一个人”这个原始句。当有人指着一个人形的物体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人时,你会毫无疑义地同意他的看法吗?当老师告诉你说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告诉了你什么?当你怀揣着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回到事物身边的时候,你已经知晓了事物的奥秘了吗?
在不思议的情形中,例句二与例句一并无差别。两句都是指出了一种形式。例句一指出了三角形的形式,例句二指出了人的形式。但是,一旦我们的目光被现实的事物本身吸引,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之所以不会对例句一产生怀疑,是因为现实中并没有三角形这种事物,或者说三角形不能作为一种事物来看。但人、马等这些东西却是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有的。请我们的思路在此停顿一下,以便弄清楚我们现在想要说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说了,现实中并没有一种叫做三角形的事物,那么我们由此知道,“三角形”这个名词并不是某种事物的名称。因此我们当然也不会被三角形这个名词所指称的事物迷惑。或者让我们再说明白一点,三角形并不是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的形式的名称,我们之所以会拥有三角形这种概念,那是完全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这种发明创造就像我们发明如锤子、锯子这类实用工具一样,它们是本来无而被我们想象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可能不理解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因为它们的存在是出于我们,我们掌握着它们的所有秘密。正如我们说上帝知晓世间的一切秘密一样。而这就是我所说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先天性的意思了—先天性就是“在概念之中”。我们了解某些事物,或者说所有被制造出来的事物,是因为我们掌握着它们的概念。因为这些事物只有在概念中才存在,所以只要我们掌握了概念(我们不可能不掌握概念,因为概念是我们创造的)那么,所有被这一概念说明着的事物都是对我们具象的。
因此,当我们把诸如雕像、房屋、钢笔、电灯等这样的普通名词用于具体的事物时,事物便在这些名词中得到了真实的说明。这些具体的事物每一个都有一种本质,它是一个是。这种本质、这个是即是它的名称,它的存在即是根据它的名称得来的。
但是另有一类事物,它们的存在却不是根据它们的名称得来的。对于这类事物,我们说它们是什么,那只是我们自己的叫法。我们给予它们的名字只是事物本身的一个记号,不可能像古人们说的那样,说是仓颉造字的时候泄露了万物的秘密,使得鬼哭神惊。中国文字确实在通灵的意义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种类事物的沟通,但是中国文化中事物的含义与西方文化中事物一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文化从物性的意义来看待事物,而西方文化是从物理的意义上来理解事物的。但是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对于那种自我存在的事物,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们,名称都与它们的存在无关。名称不可能像咒语一样,消解或者创造出一样事物来。
对于这类自我存在的事物,我们说它们姓什么叫什么都是毫无根据的。这类名称可不像例句一提到的那种类型的名称一样确确实实标注出了事物的存在。例句一所拈出的那些普通名词都是一些真正的概念。但是例句二所拈出的这些普通名词,即我们给予这种自我存在的事物的名称,人、马,等等,你究竟是打算把它们作为概念,还是把它们只作为一个纯粹的名称、一个代号来对待呢?这里切忌模棱两可。如果我们采取了后一种态度对待这些名词,那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探究事物存在的打算,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放过不论;如果我们是采取前一种态度对待这些名词的,那么我们这里就要追问根据的问题了。
我们说过不思议的情况,那是把人工造作的事物与自我存在的事物混同起来了。然则我们却无法容忍这种混同。因为这两种事物事实上并不是同一类的:其中一种没有自我存在的性质,另一种却具有这种品性。即使它们真的都是受造物,但至少我们对后一种事物的受造过程是不清楚的。因此能否把后一种事物的名称像前一种事物的名称那样当做概念来对待是大成问题的。但事实是我们确实就是这样干的。在此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颟顸的:我们不顾或者说忽略了我们没有这样干的根据。
由于这种混同,使得我们在处理两类事物的存在的问题上采取了同一种思路。我们没有注意到,在例句一中讨论存在的时候,是概念行之于前,而事物出现在后。而例句二所讨论的存在则刚好相反,是事物出现于前,而概念行之于后。这种概念后行于事物的必然结果就是形而上学的产生(我们为什么逃不出形而上学,症结全在于此)。因为概念先行于事物,所以当我们回答一个具体的事物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概念。概念从逻辑上保证了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会出错。
因为所谓回答问题,就是把某一事件或某一事物纳入到某个概念系统中去处理和说明。回答问题,就是最终念出某个概念,或者,说出某个最终的概念。这就要求某个概念在某个特殊的层次上是最终的。也就是说,它是自明的。或者我们采用一个逻辑哲学的说法:任何正确回答问题的方式都是分析性的。
但是概念的自明性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比较一下例句一和例句二所拈出的两类普通名词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会知道,所有具有自明性的概念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构建。这说明只有那种描述人工创造的事物的概念是自明的。
假如我们将自我存在这类事物的名词与以上提出的名词等同看待,那么描述自我性事物的概念亦可以是自明的。这样使用描述自我性事物的概念也就是把这种事物和制造的事物等同看待:我们可以将现成的形式从事物身上提取出来,做成关于事物本身的概念,让事物本身在这些概念中得到说明。这样做,我们是走上一条独断的道路。
这条独断之路的错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对于事物的起源是无知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存在着这样一些现成的形式。所以事物也就不会听命于我们加给它的名称的摆布。无论我们说什么,事物都不会对我们作出回应。我们只能满足于自己的想象,是对是错,都只能由我们自己去论证。
那么,这条独断的道路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理解事物的时候唯一可供选择的呢?可以说是的。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从理论上将人工的事物与自我存在的事物的差异性揭示出来。因为它们在存在的表征上并无不同。即是说它们作为事物的本性是相同的。只不过其中一种被认为是有灵的,而另一种是无灵的、僵死的。
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认知能够进行下去,为了使我们对那些自我存在的事物也能够有一种认识,我们不得不对同一种思路进行绝对性的加强,哪怕是让我们的推论失去逻辑上的可理解性。比如我们在那种自我存在的事物身上引入一个灵魂的观念,再在事物的概念中引入一个实体的观念。这样一来,由灵魂加上一个物质性的身体,事物就是事物自身,即自我存在的事物了。而事物之所以能够被我们认识,也就是因为它是某种实体。这个实体现在为我们给予它的名称所标注,这个名称同时又可以作为概念被我们理解。
但是,通过引入灵魂和实体的观念,我们的问题就真的得到解决了吗?
现在我们再来问问事物是什么。我们问:那种被你叫做人的东西是什么?那种被你叫做马的东西是什么?如此等等。我们发现,问题依然还存在,它并没有被触动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新引进来的这两个观念我们并不真的理解。
就灵魂而论,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赤裸裸的灵魂,谁也不能断定灵魂是否真的存在。并且即使我们见过像事物一样存在的可感知触摸的灵魂,我们怎么就知道它就是我们现今所理解的那种灵魂呢?即我们认为那种灵魂使事物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灵魂之不可理解,关键更在于,如果灵魂存在,那么灵魂必然是一种事物,而凡是事物(除了在我们的概念运作中涌现的即人工创作的)都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事物永远面临着解释的需要。我们需要灵魂,是为了解释事物的所谓生命现象,是为了要使得一团僵硬的物质如它们被实际观察到的那样活过来,获得运动它们自己的能力。但说到底,它们毕竟只是被推论出来存在的东西,我们永远无法验证它们的实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