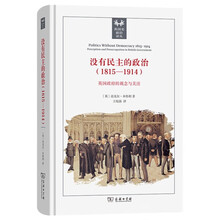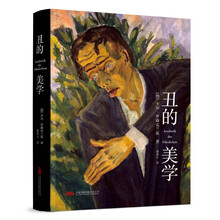与辛格和黑尔一样,我认为,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一般化原则本身已经是康德所谓绝对命令的一个本质的方面。但我要立即补充的是,一方面,康德的“理性的事实”并不能还原为这种一般化原则;另一方面,即使借助一个附加前提(诸如辛格的“后果原则”),也不可能从这种一般化原则推衍山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澄清一般化原则在何种意义上是康德的道德原则的一个本质的方面:绝对命令要求我只应当桉照我同时能够意愿它作为一种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动。但是通常说来,我能够意愿它作为一种普遍法则的东西实际上是由我自己的——经常是现有的——规范信念决定的,特别是由我对他人的——由社会确定的——规范预期所决定的。就此而言,绝对命令最终指的是:“做你认为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情”,或者甚至是“不做你认为一个人必不能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事涉规范时,别把自己当作例外”,或者直接就是,“做你应当做的”。我认为在这里指出如下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即使按照这种——差不多是基本的——解释,绝对命令也已经提出了一种无论如何也不是平淡无奇的要求,即我应当按照已经得到承认的规范义务行动,而且我应当在此时此地不自欺地这样做。当康德认为这一公设简单明了但又不易实现时,他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如何,按照我自己的规范信念行动,这样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我每次都得为我的行动提供一个适当的辩护;它也不意味着我应当按照在每一种情形中我都能当作规范的信念而行动。毋宁说,这包含了一种难以实现的要求,要求我在面对以下问题时不应当自欺,该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和他人交换角色,我对他人究竟会有怎样的期待。
的确,正如已经强调过的,绝对命令不能被还原为这种基本的含义。绝对命令正是用来解释通常蕴涵在任何“规范信念”之内的绝对“应当”或“必须”的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解释成可合理地理解的“应当”或“必须”的可能性。只有通过这一途径,绝对命令才成为一个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对于所有的“理性存在者”来说,一般化原则本身可能都是一个有效的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必然把普遍主义规范与其他规范区分开来的原则。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