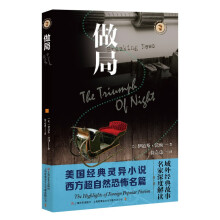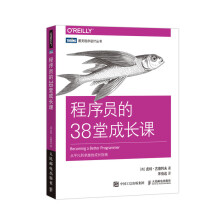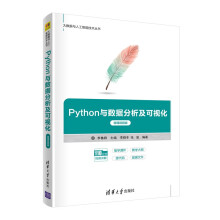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比如说用一个方块字来表示元素钨与钍,这就造成了没法形容的混乱。我们必须承认使用汉字来翻译化学术语是一个相当费力的工作。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中国文字实际上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我相信,在使用元素或者化合物的名称时,中国人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只有当他们采取国际通用符号,使用拉丁或俄文字母表示时,中国科学家才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中国的科学研究是按照苏联的模式组织起来的。正像在苏联,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研究所里,而不是在大专院校里进行的。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第一任院长是郭沫若,一位历史学家。科学院负责管理在京和在外地的研究所,后者由分院领导。科学院还有一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图书馆。同时还有许多专门研究应用科学的机构,但是它们直属中央各部领导而与科学院无关。
科学院的巨大行政机构通通归院长和五位副院长领导。他们在院部的下属不是由科学家或学者,而是由党内官员组成的。我时常要与一位显要相见,就是吴有训。他是负责物理、数学、化学方面的副院长。他清瘦,行动敏捷。在美国留学多年,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物理学家。如果不是官样文章糟蹋埋没了他,他是能有一番作为的。他不再搞研究,而是专门从事“科学规划”。总是为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错误,进行自我批判。然而看起来他并没有失望,似乎好日子就在前头,最终有一天,他还会去搞科研。因此,看起来,他的兴致总是很高的。
我还和科学院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王拓同志多次会面。他的负责苏联事务的助手是一位35岁上下的女士,我们称之为程( Cheng)女士,是位生性活泼,长相看起来相当敦实的人。 科学院官员老是开一些大会小会,研究科研项目。这些会的主要目的看起来就是为了将政府指示传达给研究所。这些政府指示朝令夕改,更改得如此之快以致科学院五大副院长根本没时间着手他们自己的科研工作。他们的时间全被所谓的“计划工作”占去了。至于院长郭沫若,他成了在官方场合出头露面的花瓶;当然每一次,少不了他在会上大发宏论。
本来中国人是能在科研工作上大干一场的,因为他们的实验室大多很大而且设备齐全,就是与苏联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研究机构很少,而且它们大多属于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一般来说,研究大多是在具有良好实验室的大学里完成的。十月革命后,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但是除了少数研究所外,大多没有现代化的先进设备。大多数实验室位于光线阴暗的莫斯科、列宁格勒与基辅的古老建筑物的院子里。只是在近来,苏联科学院才在莫斯科的城墙外面建成新的实验室。
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1949年以前建于北京、南京和昆明的大学,四周全是草坪、树林和花坛点缀的美丽景色。就是新建的研究所也是出奇的大,并附设花园草地,空间十分宽敞,这与中国大城市周围可耕地十分短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别近来已经减弱,因为部分大学里的空地已经改为供应学生饮食的小卖部了。即使如此,这些广植林木的地区仍然使得大学里的建筑物看起来十分可爱,因为它们周围往往是花团锦簇,落英缤纷,精心地用树木、绿草和鲜花装饰起来。
除了我工作的化学所,我与科学院的分支机构以及其他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也多有接触。有色金属研究所的一些人经常来找我研讨他们的一些问题,而我本人也多次去他们所。由于我在有关稀缺金属会议上的讲演,有关部门决定我的建议必须首先在铂金属领域里实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