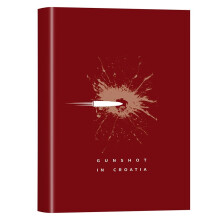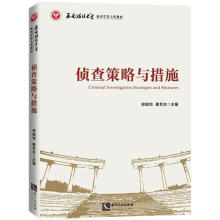报应论经历了神意报应、道德报应直到法律报应三个主要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截然明确的先后时间划分,而且在不同学者的理论上这三种报应论还常常掺杂在一起。
神意报应主要盛行于中世纪时期,主要是将刑罚的目的视为神对普通人违反宗教经典所犯之罪的惩罚和报应,即神罚报应观;此外还有将刑罚目的部分视为犯罪者要通过刑罚之报应为自己的行为赎罪的观点,即赎罪报应观。从神的角度看,神意报应论体现了神罚的特点,从凡人的角度看,神意报应体现了向神赎罪的特点。而国家和宗教机构作为神的代理机关,当然可以“替天行罚”,来将神意报应贯彻到国家和宗教机构的刑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就不能再行私力复仇,因为当时的宗教观认为私人不是上帝的代理人。这可从《圣经》支持报应的“以血换血”说法(《创世纪》9:6)、但不支持私力复仇的“不应复仇”(《利未记》19:18)和“复仇在我(上帝)”(《罗马书》12:19)中看出。
因为作为判断犯罪与刑罚的宗教经典规范有相当多的内容同一般道德原则混同,所以道德报应借助神意报应存在并发展。道德原则借助神意得到有效的维护,间接成为刑罚的报应目的,所以道德报应一开始就表现为神意报应的一部分或者说衍生形式。而在中世纪之后的宗教势力相对衰微、道德逐渐世俗化的过程中,几乎后来所有的报应论者,从康德到布莱得利(Bradley)都强调了犯罪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culpab_1ity)对于报应主义刑罚的基本地位。报应主义者都将犯罪在道义上的过错或者说主观可谴责性作为刑罚的基础,刑罚的目的就是针对犯罪行为道义上的过错和可谴责性施加报应。因此道德上的可谴责性的程度也视为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和刑罚的轻重有关。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越强,犯罪越严重,那么刑罚相对更重;反之亦然。刑罚除了作为对犯罪的道德过错的报应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目的,否则就不符合正义原则。布莱得利对此有经典总结:“刑罚仅仅是应得的处罚……不应有其他原因;如果实施刑罚是除了道德应报之外的其他原因,就是彻底的不道德、悲哀的非正义、罪恶的犯罪,不应为之。”道德报应的观点可以说是报应目的论的基本依据之一,之后发展出的法律报应也很难完全摆脱道德报应的影响。道德报应从本质上将刑罚仅仅视为对已然之罪的道德谴责,刑罚目的指向罪犯个人内在的道德人格和道德责任之回复,刑罚的报应恰恰是人自身的理性尊严的要求,对罪犯的报应恰恰是为了恢复其作为人的基本理性和固有道德感。
但是随着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和独立、法律成为社会主要控制手段,法律报应还是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于道德报应之后的新报应观,并在法治背景下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法律报应认为“报应预先由法律规定并与犯罪之严重程度相对应,其不是为了报偿或者满足被犯罪伤害的被害人而施加的——即便其有这方面的作用,而是为了执行法律和恢复法律秩序”。与道德报应内在指向不同,法律报应论的指向是人之生存其间的外在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其前提是个人有义务遵守的法律之规定,从而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得到维护。而犯罪是对法律之破坏和社会秩序之威胁,从而破坏了犯罪人对社会应该背负的个人义务,而刑罚作为对犯罪之法定报应,就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从而最终维护社会的稳定存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