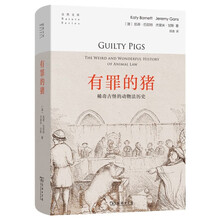一般的看法,所谓“礼教”派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对《新刑律草案》的个别条款提出质疑的张之洞和劳乃宣,而所谓“法理”派和“趋新”派的代表人物即主持制定新律的沈家本。实际上,既然“法变”是整个“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一具体人物的新与旧,恐怕就不能局限于其关于一两个特定法律问题的见解,而应看其对“法变”的整体看法,更应进而考察其对清末最后十年“新政”的基本态度及其整体表现。<br> 近年史学界对西潮激荡下晚清思想、社会大变局的研究已更深入,特别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朝野主流思潮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过去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通常倾向于将其说成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实际上,如果没有学习西方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世人所考虑的问题。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作,其中讲“西学为用”的篇幅即多于讲“中学为体”者;而且他在序中明言,中学也以“致用为要”,可知全篇都重在一个“用”字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目的和重心显然都在“西学为用”之上。<br>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张之洞已说明,这一切变革都应在坚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这不仅是清廷维持其统治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础,沈家本等主持修律者对此并无异议。因此,坚持原则上的“中学为体”并不掩盖张之洞在实际操作层面仍落实在“西学为用”之上。更重要的是,张之洞在《劝学篇》进而指出,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这是一个关键。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理解《劝学篇》与前面所引的刘、张二人的“变法三折”的思想关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