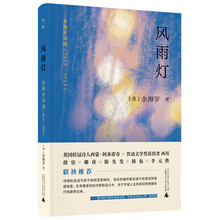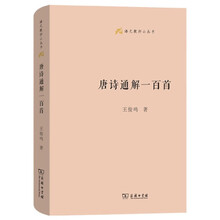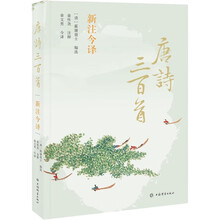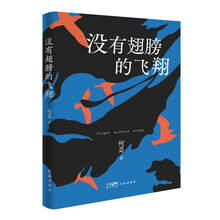人们以为日常事物离诗歌很近,这多少还能理解。但假如一个诗人以为日常事物离诗歌很近,这就不可原谅。日常事物常常是在诗的尽头才出现的。日常事物对诗来说常常是神秘的。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熟悉,并不能取代日常事物给诗带来的那种神秘的含义。
写日常事物的诗,不可能仅仅凭借风格的力量达到诗的效果。写日常事物的诗,,必须同时意识到它自身也在写关于奇迹的诗。
从风格意义上看,日常事物是诗的奇迹的一种变体。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日常事物或许只是诗的奇迹的一种效果。
在诗歌中,最野蛮的词,常常有最温柔的用法。
诗的批评,既是一种社会批评,也是一种自由关怀。
但对有些诗人来说,由于着眼于自由关怀的深度,社会批评渐渐演变成一种诗的审美用途。
对语言的距离的组织,也是诗的社会批评的一种表现。
距离的组织,可以是一首诗的题目。比如,它是卞之琳的一首诗的题目。它也可以是一本正在写作的关于现代诗的结构的书的名字。
距离的组织,是想象力和经验在诗的结构上达成的一种默契。
新诗史上,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既是一首优异的诗,它达到的诗歌水准足以可与斯蒂文斯媲美。同时,对我们的诗歌美学史来说,它又是一部微观的现代启示录。
《距离的组织》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对一种现代语感的把握。夸张一点说,在卞之琳的这首诗中,半个新诗史的内容都被这种语感浓缩在了一种现代诗的自觉之中。
诗人的幽默是一种可疑的幽默感。正如诗的幽默是一种可疑的幽默。
从体裁上看,诗是一种关于希望的并且很少偏离希望的体裁。
无论是从风格的意义上看,还是从诗歌责任的角度讲,美都是诗的一种神秘的礼物。
美是诗给诗人带去的一种神秘的回报。
美是诗的一种动静。
动静小一点,美对诗的想象力的刺激也相对要小一点。动静大一点,美对诗的内容的刺激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彻底的释放。
诗,是诗的稀有的品质。
不过,这种稀有,并非意在引发我们对诗的品质的绝望感。而是说,诗是以严肃的游戏为终极的自我实践。就像凭借生活经验观察到的一样,任何稀有的东西,在本质上只是人生的游戏性的一种喜剧的反馈。也可以这么说,稀有的东西只对人间的喜剧负责。
不写诗的人有时会和诗人一样对诗句的长短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一行安排得这么短?为什么那一行安排得那么长?其实,从艺术的角度看,诗句的长短就像绘画中的线条一样,该长的,自然就会显得很长。
诗句的长短,与其说是由诗的音乐性来决定的,不如说它是由诗人对诗的规则的自觉程度来决定的。
诗句的长短,有时只是诗人对诗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想象性的实验。
表面上可以很随意,其实,它们仍然受到诗歌史语境的隐秘的有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史趣味对诗人的催眠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的默认规则对诗人的自由发挥的修正能力。
与人们期待的正相反,诗的自由常常意味着诗人的不自由。
有的诗人终生都不适应诗的这种矛盾。而有的诗人则迫不及待地欢迎这种矛盾。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