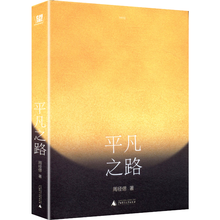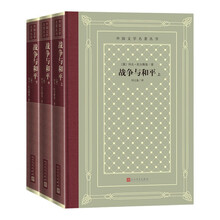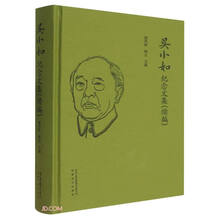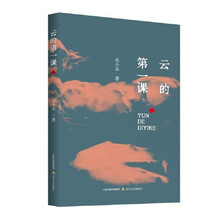什么时代,什么队伍,也重视学历和资格。不练也不要紧,学历在那里摆着,资格一年比一年老。
一九四三年,我们一同到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他在美术系做研究员,我在文学系。正在整风过后,学院的学习,并不紧张。夏大,我们一同到山沟里洗澡、洗衣服,吃两红柿。他有一把妇女们做针线用的剪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直放在书包里。我们头发长了,他给我理,我给他理。我很少看见他读书,或是画画。但谈起来,就滔滔不绝,他的美术方面的知识,还很是渊博的。
他告诉我,他正在追求文学系的一个绥德来的女生。延安生活,非同敌后,吃得饱,又安定,滋生这些欲念,是很白然的。但男性同女性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恋人,都是长期处在一种游离状态,不易明朗。杨墨的事情,也是这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忽然宣布投降。十五日晚上,延安军民,狂欢庆祝,火把游行。我思念家人,睡下的比较早,半夜之间,杨墨来了,告诉我,他的事情,已经在延河边成功。先是挨了一个嘴巴,随即达到目的。说完又匆匆走f。
后来我才知道,爱情,有时也会像行情,战局的突然变化,使交易所的某种证券,立刻跌落了很多。人们就要奔赴各地,原有妻子的,也有望重新团圆。原处于极端矜持状态的女同志,以其特有的敏感,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纷纷向男友们,张开了怀抱。
我出发了,目的地是华北。杨墨因为还有一些纠葛,暂时没走。
我回到家乡,第二年,父亲病故。有一天,杨墨来到我家里,说和那个绥德女子结了婚,在路上,她又跟别人到东北去了。我没有仔细问。我想给父亲立个墓碑,请他设计一下,就把他安排在外院,和我的一个堂叔父同住。
这问小屋,每晚总是有一些人来闲谈。问到杨墨还没有家室,就有一位惯于说媒的大娘,愿意给他介绍。正好村中有一位姑娘,是妇女队长。村中两派不和,有一派说她和武委会主任不清不楚。这本是为了打倒武委会主任,却连累得这个农家姑娘,上城下界,对簿公堂。家里人觉得难堪,急着把她聘出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