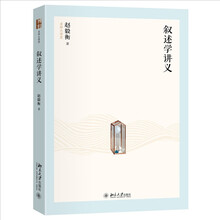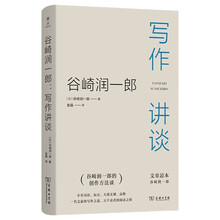最后看看对商品(小说)的认识情况。中国古代的文学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诗”、“文”是最早的文学体裁,因此成为“文学”的核心,而后起的文学体裁往往遭到正统士大夫的轻视,如“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逐渐降低。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则遭到鄙视,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便是说它们“俗”得很。近三四百年来,尽管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早已说小说所用的白话,小说也不断出现杰作,不断有士大夫出来赞美小说、提倡小说,然而这终究是少数人的意见,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小说的看法。一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前,如黄人所说,在士大夫圈子里,对于小说是“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元明清三代都要禁毁小说、戏曲,清代尤甚,几乎历朝都要下令禁小说、戏曲。这种禁毁也往往得到士大夫们的支持拥护。有些士大夫认为,写小说和赞美小说都是一种“造孽”行为,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们不是应受“杀头之报”,就是“子孙三代皆哑”,或者披枷戴锁在地狱里忍受各种苦刑的煎熬,受到各种报应。士大夫为文之所以用古奥的文言,为的是将思想保持在古人的轨道,按古人思维的模式思维,防止在思想上离经叛道。正统文学正是以“雅俗之分”将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它必须把“雅”作为文学形式上的标准,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在明清,认识几千字,哪怕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几十万字的白话小说,也算不上“文人”;只有能读文言,并用文言做合乎士大夫标准的文章,才能跨入“文人”的行列,才可以应试,有希望做官。于是,士大夫十年寒窗苦读,学的就是运用先秦的语言创作文学。文言不仅制约着思想,也维护着士大夫队伍的纯洁,成为士大夫专用语言。
真正促使士大夫阶层接受小说,把小说当作“教化”工具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康有为于19世纪80年代路过上海时,从点石斋打听到书籍销售情况是“‘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于是得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的结论。他又从《万国公报》中看到傅兰雅提倡“时新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中国的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由此萌生了利用小说“教化”的设想。在了解日本维新变法时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要将小说纳入维新变法的轨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政治小说及其理论研究,写出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着重阐述了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后来他在《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等一系列文章中申说他对政治小说的看法。他还亲自动手翻译了《佳人奇偶》、《经国美谈》和《十五小豪杰》等外国政治小说。1902年11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办小说杂志《新小说》,继续鼓吹“小说界革命”,推动小说创作和小说美学的近代转型。“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梁启超对小说的本质、功能以及小说界革命的目的、方针和运作等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