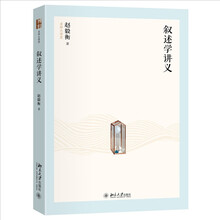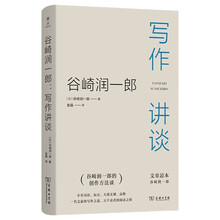这些日子留给我的记忆,也同样的复杂和充满歧义。但有一点倒是十分清楚,这就是后来不必借助更多的理论,就能懂得“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不必费太多的气力,就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对许多事情,我到现在还是懵懂无知,但这几十年来,上演着的“历史”不断改写,不断“颠倒”、“拨乱反正”、再颠倒的戏剧,想忘也忘不了。这些见闻,这些体验,对我来说,“好处”与“坏处”几乎同等。既有助于我从原有叙述中发现隐蔽的缝隙,作为思考的起点,也由此滋生了某种“虚无”、冷漠的倾向。当然,“虚无”也不是真的。因此才写了一些书,一些文章。而且在有的时候,还会焦躁不安、劳心费神地想“重建”看待历史、现实的“连贯性”,将思想、感情的零乱碎片加以拼接。虽然这种努力往往没有实现。
三、在你的论著中,有时能感觉到一些互异的方面,但你似乎能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给予处理,赋予一种持续的张力。虽然你认为自己常常犹豫不定,但这种方式在客观上却保存了文学与历史的复杂之处。比如,你现在的研究思路似乎与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关注中国文学现代性特殊经验的思潮有相呼应的地方,但从深层的对文学的理解来说,似乎更倾向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对文学的多元化也抱有期待,文学趣味上也有一种精英化的取向。又如,在研究方法上,你能够接纳十多年来许多新的理论、方法,并将之引入对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与实践中,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突破旧有的局面,另一方面,你对文学的价值也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对文学的独特性情有独钟,等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