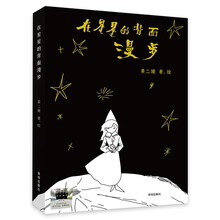从“小犯人”到继父的宝贝
在我心中,“父亲”的概念,一度跟痛苦和绝望联系在一起。
在河北省那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就因为父亲的突然入狱而结束了。那年我才四岁,眼睁睁看着父亲被警察从家里带走。他脚步踉跄,面色苍白,回头看着我和仅仅一岁的弟弟,满脸是泪。
家里已经是山崩地裂,母亲搂着我们,蹲在门槛边失声痛哭。
父亲因误伤他人被判刑八年,从此我和弟弟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我们受尽了村里其他孩子的白眼和谩骂,“小犯人”成了我们的绰号。在学校我们被孤立,回家的路上又常常遭到偷袭,被一些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趴在渗透着青草味的泥土上,我哭着大喊:“爸爸,你快回来啊!”
三年过去了,我们渐渐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甚至已经忘记了他的模样。可有一天他却突然回来了,是被人用担架抬到自家炕上的。在监狱的例行体检中,父亲被检查出患有“肝癌”,而且已到晚期,被允许回家做最后的团聚。不久,这个病人膏肓的父亲撒手而去,撇下了悲痛欲绝的母亲和懵懂无知的我们。白天,母亲强打精神下地干活,给我们姐弟洗衣做饭;晚上,她精神恍惚,蜷缩在那间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整夜发呆。
父亲去世一年后,有人来家里替同村的张福朋提亲。经不住三番五次的劝说,也为了让我和弟弟有个照应,母亲答应了这门亲事。
于是,母亲选了个好日子,就带着我和弟弟搬出了即将倒塌的旧房.住进了张家。
张福朋是个老光棍,这个强壮、高个子的男人,从小就是孤儿,长大后也不善与人交往,憨厚到有些木讷,因此一直娶不到媳妇。结婚那天,他穿得很光鲜,看见我们就“嘿嘿”地笑,看见母亲就把头低下,腼腆得像个大姑娘。
我们看他红着脸傻笑,觉得很有意思,也朝他身上丢花生和瓜子,跟旁人一样起哄。
真正开始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母亲和我们都感到了久违的幸福。继父多年孤独一人,所以特别珍惜这个新家,他体贴母亲,疼爱我们,甚至超过了我们的生父。
有一次我被人欺负。额头上被打破了个小口子。继父扛着锄头回来,看见我嘟着嘴巴。就故意装成木头人,直着腿和胳膊走路,逗得我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淘气的弟弟爬到邻居家的果树上摘果子吃,被人家发现了,还是继父给火冒三丈的邻居赔礼道歉的。弟弟怕挨打,躲到母亲身后,继父却乐呵呵地说:“下次想吃果子,我给你们弄去。别再拿别人的东西,那样不好。”
继父从不打骂我们,只要有好吃的,一准给我们留着。我和弟弟渐渐淡忘了丧父的不幸。每天背着小书包,昂首挺胸地去上学。
继父刷新了“父亲”的定义,重新给了我们幸福的时光。
继父成了我们唯一的亲人
两年后的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课,突然被班主任招呼出去,他沉着脸让我赶快回家。我心跳加速,飞快地跑回去,在门外就听到继父压抑的哭声。
母亲居然去世了!原来,上午她在田里突然晕倒,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扑上去抱着母亲,摸着她不再温暖的脸庞,整个人被一种天塌地陷的恐惧和绝望包裹着。不由得放声痛哭。
母亲走了,我和七岁的弟弟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继父还会要我们吗?不知道哭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时,继父红肿着眼睛守在我身边——他面容憔悴,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继父更加沉默,我和弟弟也变得小心翼翼,每天看着继父的脸色生活,害怕有一点点过失就会被遗弃。继父很快就发觉了我们的变化。有一天吃完晚饭,他放下碗筷,看着我和弟弟认真地说:“孩子,你们的爸妈走了。我就是你们的爸爸。我们一直是一家人,我不会不管你们的。”弟弟“哇”的一声哭了。继父一边用粗糙的大手给弟弟擦眼泪,一边尽量轻柔地说:“你们只管好好学习,别的我来想办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