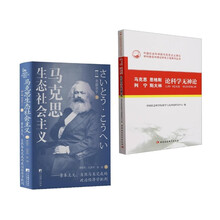掌上千秋史
答《天涯》杂志社问
载《天涯》杂志,2011年第4期
一,在我看来,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和《天下》都呈现出一种“光明史观”,它区别于长期流行的中国“阴暗史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专门讨论),特别是,您强调中国的天下制度有其制度优势,而并非仅是专制独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能否最简要地概括中国长期历史的光明面?并简要概括这些因素如何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支撑?
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的“天下”制度确有其特殊的优势,我个人以为:所谓中国“天下”,由内地、边疆和四夷这三个部分的互动构成,而针对这三个组成部分,形成了高度特殊而灵活的制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郡县治理内地,以封建治理边疆和四夷。
例如汉代就是这样,所谓“边各自备,内郡专刑赏”,唐代也差不多,“内则诸卫将军,外则节度总管”,中国历代王朝平均下来有二百多年的寿命,秦、汉、唐、元、清更是欧亚大陆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帝国,这种政治奇迹的发生,当然靠的是制度优势,靠的是纲纪和法度,所谓纲纪法度,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政治路线、制度优势,而说到底,它靠的就是这种融郡县与封建为一体、融内地与边疆为一体的灵活而特殊的制度。反过来说,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危机,也主要表现为天下制度的危机:比如说,唐把治理边疆的封建制度用于治理内地,结果造成边将权重,遂致末大之患,内地则裂为藩镇,中央无能为力,导致军阀混战;而宋的偏颇恰恰相反,则是以治理内地的郡县制度治理边疆,以文官知州事,一切军事、财政、税收之权归中央,地方和边关陷入无能,于是在辽金的袭击下不能自保。
二,您特别推崇一些历史人物,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更把王阳明的主张与毛泽东联系起来,更可谓“今人之中,独推毛泽东”,为什么?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选贤制度,即通过考试来从平民中选拔人才;这个制度从南朝梁武帝肖衍的时代就已经在尝试,到了唐代,就成为国家正式的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是好,我们历来重视教育、重视文化,自然就是这种制度好的一面的体现,不过这个制度另一方面来说也不那么好,因为如果考试和选拔的内容完全脱离现实、脱离生产劳动,脱离政治、经济、司法,那么选出来的就一定是大批的废物。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总起来说,就是这种选拔机制的产物,由于他们脱离现实、鄙视生产和实践,所以中国就不能产生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晚清的郭嵩焘曾经这样刻薄地说:“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今天看来,中国的士大夫,大部分属于乡愿,即他们读书不是为了求真理、求信仰,乃至求知识,而是为了求功名富贵,乡愿的主要特征就是媚世;当然,还有少数一部分是狂生,即狂放不羁者,他们有着磅礴的才气、甚至有着卓越的理想,但往往受到社会压制,怀才不遇,于是就把一腔才华、怒火全部转化为批判,结果他们一辈子都在批判,但却忘记了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更有极少数属于所谓“狷者”,那就是看破功名利禄、也看破红尘,从而转向内心修炼,“冷眼向洋看世界”,幻想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成为世外高人。
这三类人:乡愿、狂生和狷者,构成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群像,只不过王阳明则是其中例外中的例外。
王阳明不是乡愿,因为他早就当官当的不耐烦了,他年轻时候可以说算是个狂放不羁的大才子,后来也曾经讲过内心的修炼,但是,他非但没有仅仅把才情转化为口诛笔伐的批判,也没有看破红尘而主张无为,相反,他把他的思想和才情转化为实践,转化为事上磨炼和为老百姓办实事。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阳明享年57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因为假如说中国的士大夫都走了阳明那重视实践、重视躬行、重视实事的道路,则可以想象,中国也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
我们知道,康德为欧洲的市民社会设置了道德法则,而实际上,阳明也力图在批判士大夫阶级的基础上,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设置道德法则,而这种道德法则,归根到底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精辟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所谓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要避免成为“乡愿”,重新思考王阳明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重新思考康德、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一样。因为现在我们也是乡愿太多,口头的批判太多,冷眼向洋袖手谈心性的太多,而主实践、主事上磨炼、主张“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样的人太少。
所谓“我心即是民心”,与民同心,斯为大同,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在我看来,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人物。
马克思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家必定是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这便是阶级社会里政治活动的一般特点,因此,政治家一定是有敌人的,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C?施密特认为他的这句话简明地说到了政治的实质。有人骂毛泽东、甚至恨不得焚尸扬灰而后快,这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当然有他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一般总是很强大的,只不过毛泽东统统藐视他们而已。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那些敌人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性的,即他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斯?韦伯将“以政治为业”与“以学术为业”作了区分,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一定是有敌人、有爱憎的,政治家是爱憎分明的,而学者只有读者与学生,学者一定是客观的,但实则不然;只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学者一样是有敌人的,马克思是如此,韦伯自己是如此,甚至不才如我等写了几篇流水文章者,竟然也是有敌人的,这些敌人同样未必是学术上的,而往往是出于政治立场使然。没有敌人的政治家不算政治家,那只是乡愿;没有敌人的学者不是学者,那只是个犬儒。
想一想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逢的难局,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扭转这个难局,靠的是一群民族英雄在人民群众中起到的先锋队作用,而在这些民族英雄中,毛泽东是打头的;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像毛泽东这样,为新中国牺牲了几乎全部的亲人,而他的后人没有一个做生意、发洋财的,“负衿而有天下,而子孙为庶人”,这样事,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话恐怕也只适合他一个人,世界上的领导人,论读书、写文章和打仗,衡文论武,哪一个能比毛泽东?随便举个例子:毛泽东能够飞鸣镝号令千军万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谁能复现这样的军事奇迹?而今恐怕能说清楚“飞鸣镝”是指什么、语出何典者,也未必有几个人。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由落后挨打走向了和平发展,这个世界上,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现在毛主席死了,有人就骂他骂的不象话,这就是典型的“打便宜拳”的国民劣根性--你看美国有那么多无聊分子骂华盛顿、林肯吗?日本有那么多人给天皇造谣吗?人说美国人讲公德、日本人守纪律,有些中国人则心理阴暗,这话不错。所以,在各种场合说一点公道话,这不过是尽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本分,而且,如果以为这只是为维护毛泽东个人那就错了,这当然不是为毛泽东个人辩护,而是维护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人民币制度、军队制度、多民族共和、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作风等,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德,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遵守的起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要什么人来辩护吗?生固欣然,死而无憾;花谢还开,长河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日月经天,何劳寻觅。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美国有华盛顿、林肯,德国有马克思,俄国有彼得大帝和列宁,中国的毛泽东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承认的人类英雄;因此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