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点点头,表示感谢。他对语言非常感兴趣,喜欢用富有哲理的方式去琢磨一个词。“很有意思,”他顿了顿又接着说,“你们英国人把懒散当做一种恶习,而我们恰恰相反,懒散通常比忙碌更受欢迎。现在的世界太紧张了,多一些懒散者不是很好吗?”
“我倾向于你的看法。”康维答道,神情既严肃又像开玩笑。
在会见过活佛后的一个星期里,康维陆续认识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相识与康维相处得不即不离。张为他们互相引荐时,既不过分热情,也毫不勉强,而康维则感受到一种非常吸引他的氛围,在这新的氛围里没有紧张兮兮的喧嚷,也没有面对延宕的失望。张向他解释说:“有一些僧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接见你——也许是好几年——但不用觉得奇怪。时候一到,他们便会准备好与你结识,他们不急于这么做并不表示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以前康维到外国使馆拜见新到任的官员时,也常有这种感觉,他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他也确实见到了一些人,而且非常愉快,同这些年长于他三倍的人攀谈,一点都没有在伦敦和德里那种强人所难的尴尬。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叫迈斯特,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支探险队的幸存者。他英语讲得不错,尽管有口音。几天后,他又高兴地结识了活佛曾特意提到的那个音乐家阿尔丰斯·布里亚克。这位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法国人看上去很年轻,却声称自己是肖邦的门生。康维觉得他和那个德国人都很好相处。他已经私下里对他们进行了分析,并经过几次更深入的会面之后,康维得出两个结论:这些人虽然外貌各异,但看起来年龄上无多大差别;再有就是,他们聪明睿智,但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全都四平八稳,很有分寸。在和他们的交往中,康维总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回应,他发觉他们都看出了这一点,自己也很是满意。他还发现,他们其实与其他任何有文化的群体一样易于相处,尽管他们在听他回忆那些遥远而不熟悉的往昔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古怪和奇特的样子。比如,有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在交谈中问起康维是否对勃朗特姐妹感兴趣。康维说一般般,于是那老者说:“你知道,四十年代我在约克郡西区当副牧师,我到过海沃斯并在牧师住宅区住过。在那里我对勃朗特姐妹作了一番全面的研究——真的,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她们的书,也许你什么时候可以拿去读读?”康维热诚作了应答。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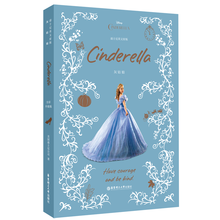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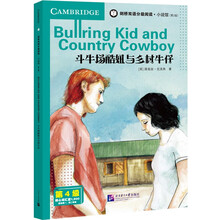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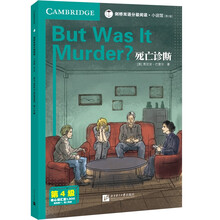
——詹姆斯·希尔顿
我们可以不指望上苍垂怜,但我们隐隐约约希望它会被外面的世界忘却。我们在这里读书、听音乐、冥想,去保存一个没落时代的脆弱光华,并寻求人在激情耗尽时所需要的那份智慧。
——《消失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