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沛教授在《文学的解放》一文中所做的精辟分析则告诉我们,即使在西方,这种所谓“文学的独立”也事实上并非古已有之。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终结论”便是其重要的哲学基础。“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因此‘艺术’的终结同时就是文学的终结。终结后的文学何为?
答案是‘自为’:终结后的文学只能是自为的文学。所谓‘自为’,即以自身为目的。以自身为目的或‘自身合目的’的文学不再以‘精神,及其在时间中的展开即‘世界历史’的目的为目的,因此是根本无目的的。自身合目的而根本无目的,这正是现代‘文学’的吊诡之处,也是它的症结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沛认为,“文学的独立”事实上变成了“文学的隐沦”。
因此,与其说从学科分际的意义上研究文学是一种“进步”,不如说这一现代性事件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某种缺失和危机。作为现代学科体制中的一员,倘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所谓内部研究具有足够引起高度重视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无疑还更应该看到,上述内外之别事实上至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真空中没有文学,我们不应该也无法真正做到对文学的“活体解剖”。
而更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单纯的学科意义上的。
文学的“自为”,文学与思想和精神的分离,文学与“世界历史”的疏远,既阻断了我们理解文学之整全的可能性,也阻断了我们透过文学理解世界之整全的可能性。
用胡继华教授在《绝对隐喻——文学与思想的中介》中的话来说,文学与思想二者完全不是互相从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绝对隐喻”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仅意味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莎士比亚既是文学家,也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家;也不仅意味着,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之国中常常有索福克勒斯、歌德、荷尔德林出没于其中;甚至,这也不仅仅意味着,莱辛既是德国现代戏剧之父,既写作《智者纳坦》、写作《恩斯特与法尔克》,也写作《论人类的教育》,而卢梭则既是《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也是《爱弥儿》、《新爱洛漪丝》和《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沉思》的作者。
我们当然必须知道这些。必须学会用阅读诗和戏剧的方式阅读通常所谓的哲学论文或思想文本,甚至必须学会不放过《战争与和平》结尾那些枯燥的历史哲学段落,并了解海德格尔在《路标》中如何解释柏拉图的“洞喻”……但我们重提“文学与思想史”研究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尤其需要提及的目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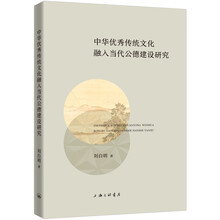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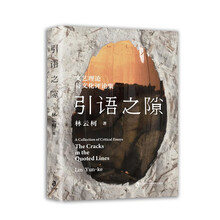





——[法]瓦雷奇·吉斯卡尔·德斯坦、艾瑞克·以色勒维奇/《中国傲慢吗?》
“复杂性的挑战”召唤一种针对“人类精神奇特能力”的最大幅度的重新展开,使我们能够聪明地使用“人类事务中的理性”。这种展开,如今我们可以从认识和文化角度进行论证,在实用和经验层面进行展示,在人类社会的探险中证明其合法性,但又不将其绝对化。
——[法]让一路易·勒莫瓦涅/《复杂地行动与思维——我们时代的方法论》
在“取道欧洲”本来是“取道”希腊将中国哲学变成了一场精神盛宴方面,弗朗索瓦·于连功不可没;他向人们展现出,阅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一再要求我们将未曾言说的内容补充进去。我们补充进去的是我们的理解,为此,有时“取道欧洲”也是有益的。
——[德]沃尔夫冈·顾彬/《方法与阅读——弗朗索瓦·于连与阐释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