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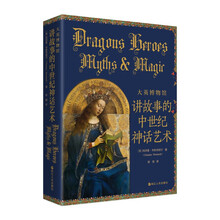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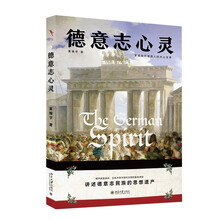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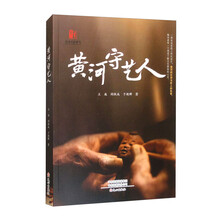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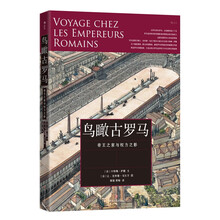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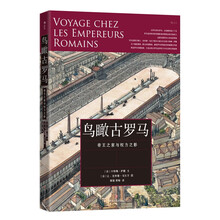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一个春日的早晨,南西·米特福德[1] 躺在床上自哀自怜。年届四十的她厌恶自己的人生——婚姻失败,写过三部无足轻重的小说,惨淡的销售成绩使她不得不在伦敦一家书店担任薪水低廉的助理。她想辞去工作,再写一部小说,但经济上负担不起。战时的食物配给导致她瘦得健康亮起红灯,现在,她正因严重的喉头发炎而卧病在床。
那天,在伦敦,烦闷无聊、缠绵病榻、沮丧泄气的南西·米特福德,写了封信给她的母亲。“我需要放个假,”她写道,“我的薪水这么低。”然后,出其不意地,她宣告:“我像疯了似的想到巴黎谋职。”她强调,这样的计划还是非常不明确的——你看得出来,这只是身为一个女儿的手段,目的是平息母亲日益加剧的忧虑。真正泄了她的底的,是那短短的一句喟叹。就在那里,那一页的下一句,独立出来的一个句子,有如歌词般的单单一行字:“噢,
为了住在巴黎,我愿付出一切!”如此这般,南西·米特福德吐露了将改变她人生的豪情壮志。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个春日早晨的破晓时分,我,蹒跚、筋疲力尽、面无血色地,走过戴高乐机场的透明通道。在飞了二十四个小时后,我步下飞机,皮肤干皱如纸,头发硬如铁丝,一身旅行装束松垮垮、皱巴巴。
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个三十出头的阿尔及利亚人,浑身散发着犹如皇室般的尊贵气质。我们聊了一下。我试着提起劲儿,张开我那懒洋洋的澳大利亚嘴巴,表演法文元音和双元音的发音杂技。“澳大利亚?”他说道,“那很远呢!”还有:“你喜欢巴黎吧?当然了,人人都爱巴黎。”然后:“我,不爱,我不住这里,太贵啦。”突然间,他羞涩而温柔地说:“我老婆刚生了我们的第一胎,是个女孩。”他举起一张小小的拍立得照片,我倾身向前赞赏那有着一撮撮黑发的棕色宝宝。
“真漂亮。”我说,“她叫什么名字?”
“桑鲁卓。”
我欣喜地坐回位子:“那个说故事的女孩?《天方夜谭》里的那个?她的名字怎么念?再念一次。”
仿佛口中淌着蜜, 他用慢得叫人融化的速度再说了一次:“桑——鲁——卓——”
真好听啊!那么的柔美,富有异国风情。我跟着他复诵一遍。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他得意地对我微笑着。
“说不定她长大后会告诉人们关于她人生的精彩故事。”
“没错。”他说,“我老婆也这么认为。”
……
德梵夫人是所有沙龙女主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但这不是我对她感兴趣的真正原因。我在乎的是她创造出什么,以及更重要的,她克服了什么。
做好心理准备吧,因为接下来是一段绝望至极的文字。“先生,至于我自己呢,”德梵夫人对伏尔泰写道,“我承认我根深蒂固、悲伤地、不幸地感到生而为人的痛苦。在这人生舞台上,不论要我扮演何种角色,我都宁可拥抱虚无。然而,你恐怕会觉得矛盾的是,当我最终必须归去时,我对死亡同样满怀恐惧。”
这是真实的德梵夫人。她的沙龙是巴黎最欢乐的沙龙,她却有着二十世纪了无生气、空洞虚无的现代情调。对她而言,一切的一切都一样,不管你是国王还是乞丐,只要活在世上就是大大的不幸;这种不幸凌驾于一切的一切之上。
德梵夫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驾驭“存在”这个难以忍受的负荷,但她无从找到安慰。即便还是个年幼的孩子时,她就看透了“神”这种概念。圣经反正没有品位,她也从不关怀大自然,乡下生活的乏味令她不耐。人际关系呢?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牵系往往是出于习惯或对彼此的需要使然,而非建立在无关利益的真诚情感上。她被安排嫁给一位乡下侯爵,在他身上或家庭关系里,德梵夫人完全找不到能赋予生命价值的东西。她的姐姐特地来到巴黎,住在附近就近照顾她。但当姐姐过世时,德梵夫人只说:“她是个好女人,但你对她不会有感觉。”德梵夫人从来不想有子嗣,还很高兴自己不曾将另一个生命带到世上,忍受这场漫长、空白、毫无意义的人生。
……
德梵夫人意识到存在所带来的道德与精神苦难,终其一生就这样痛苦地活着。她的因应之道呢?当然不会流于老套,不是自杀,不是宗教信仰,不是通过酗酒或吸毒来转移注意力,都不是,她选择了最不可能的生存之道,她选择了社交、欢乐以及理性。
德梵夫人将沙龙规范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她扬弃直觉、感性与自然之美,而选择逻辑、理性与人为艺术。她孜孜不倦地投入维护贵族的生活规范,这种规范的基础是广博的学识、简单的公平原则和信手拈来的机智。社交生活若非她的救赎,至少也成为她的止痛药。
……
——《悉尼先驱晨报》
《自由、爱与欢愉》不止是一部自传或回忆录,它更是一本温柔的指引,教你跳出平凡的视角,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生。
——《Lime light》杂志
作者充满热情的描绘让我们深深地为这些超凡女性的人生着迷,也让最熟悉巴黎的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这座超凡的女性之都。《自由、爱与欢愉》是一趟引人入胜的旅程——对露辛达来说,想必也是一趟自我发现之旅。
——《Vogue澳大利亚版》巴黎编辑查拉·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