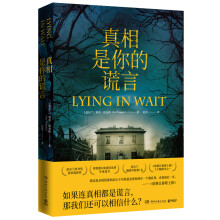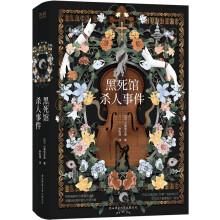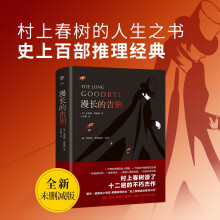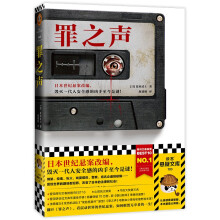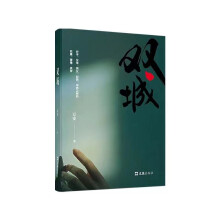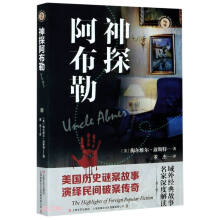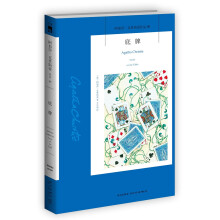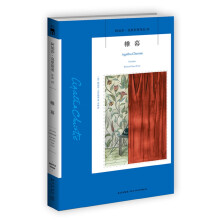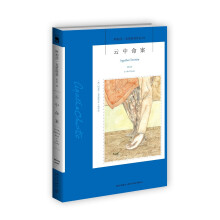没有发生毁盟是各类因素的结果。譬如说家康在1584年对秀吉不成功的挑战,就显示出坚定的反丰臣联盟不可能成立。秀吉对手之间利益的分化,当群体抵抗最具实效时,又缺乏一个反丰臣的联合阵线,使得秀吉势力日益巩固,终于让背弃早期的盟约成为一种蛮干之举。而且1580年代的主要大名们,均为守旧之辈。作为地方豪强,消耗战肯定损失连连,他们选择支持一位熟悉的、倾向于核准他们的土地索求,并且对他们所施加的个别或者集团压力疲于应付的领袖。对外样大名通常温和的行为显得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当中一部分自愿参与秀吉最初的超越织田边界的战事。他们为同伴树立了联合的榜样,并且警告丰臣联盟中三心二意的成员,反叛可能招致不止来自秀吉谱代大名的报复。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外样大名如毛利家族无可比拟的合作,给秀吉式和解创造了条件。他们为秀吉早期的战事提供兵力,通过其忠诚展示联盟的效用,因而鼓励秀吉向外接纳新的盟友,被征服者也一样。秀吉对那些外样大名如此感恩戴德,他继续分给他们战利品,而不是给谱代大名,后者才代表其政权的根本特质。
但是战争的策略逻辑仅能部分解释外样大名的忠诚,而且也不足以理解,为什么面对强化其家族势力的巨大机会时,秀吉依然继续恪守对外样大名的承诺。正如《太阁记》的作者们关注命运的诠释功效,对联盟合理性的马后炮式的探索,给惊人的突发事件涂上必然性色彩。战国时代的教训充分显示,对长达一个世纪的内战的军事解决,并不一定非既成的状态不可。信长通过征服的曲折性扩张和秀吉和解的经验,其间形成截然对照,在此值得进一步省思,因为在前者治下的恐怖和后者政治整合的意愿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信长从摧毁幕府体制开始,走向以灭绝威胁他的时代所有的领主。他于是给秀吉留下了恐怖性遗产。如果没有这一遗产,有多少大名会冒险加入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秀吉时期对安全的寻求,代替了对征服的欲望。目标的移置,以及因此而来的理念的转换,如果没有一个恐惧性背景,依然是难以解释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