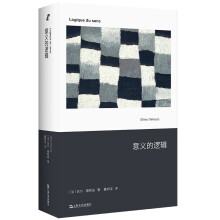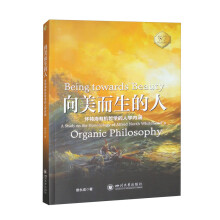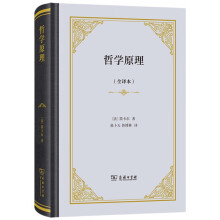刚刚在几天前,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结果发现,我对公众之会回过头来倾向于我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甚至是下一个世纪的公众,也不会倾向于我,因为他们都是按照那帮引导他们的人的眼光看我的;而引导他们的那些人,是一拨又一拨地不断从那个憎恨我的群体中产生的:个人虽然死了,但群体没有死,他们原来的那些看法还依然存在,他们像魔鬼附身似的仇恨心还照样在活动。即使我的敌人作为个人全都死光了,但医生和奥拉托利会会员总还有活着的。即使迫害我的只是这两个群体,我估计,在我死后,他们也不会让我得到安宁,他们也会像我在生之时那样对我。也许,由于时代的变迁,我真正得罪过的医生们会平静下来,不再恨我;但我曾经爱过、尊敬过和信任过而从未冒犯过的奥拉托利会会员,这些基督教的教徒和半僧侣似的人,是绝不会手下留情、就此罢休的。由于他们自己的不公正而造成的我的罪过,他们反而自以为是,不原谅我,因此,被他们千方百计加以笼络和煽动起来的公众,也将同他们一样,是不会偃旗息鼓、就此收兵的。
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结束了。人们从此既不能对我有所助益,也不可能对我有所不利。在这个地球上,我既不希望什么,也不害怕什么:我在地狱的最深处,反而最宁静;虽然成了一个可怜的倒霉鬼,但却和上帝一样,对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无动于衷。
从此以后,对我身外的事物,我都毫不过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既无亲友,又无兄弟。我虽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但却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人。虽说我周围有一些我熟悉的事物,但它们无非是一些令我伤心和痛断肝肠的东西。我不想看我周围的一切,因为它们没有一样不是使我感到鄙弃,便是使我感到痛苦。因此,应当马上把这一切使我感到难过而又无益的令人心酸的事从我心中彻底排除,既然我只有在我自身才能找到几许安慰、希望和宁静,我便应当独自一人安度余生,只依靠我自己和关心我自己。正是在这种心情下,我才又接续写我的《忏悔录》,真诚和严格地审视我自己。我要把我一生最后的时光用来研究我自己;我要及早准备我应当向我自己作出的总结。现在,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与我的心灵进行的亲切的对话,因为,只有与我的心灵的对话,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我进行的。我要对我内心的活动进行缜密的分析,把它们清理出一个很好的头绪,改正其中尚存在的缺点。我这样潜心思考,不至于完全没有用处;尽管我在这个世界上已不可能再作出什么贡献,但我绝不会浪掷我余下的时光。我每天散步的闲暇心情,往往充满了令人神往的对往事的回忆;遗憾的是,我把它们差不多都忘记了,因此,我要用笔赶快把我还能想起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以便今后拿出来重新阅读时,能从中得到快乐的享受。我要把我过去的不幸、我的迫害者和我受到的屈辱通通忘记,只回忆我的心配享受的奖励。
这些记录,严格说来,只不过是我的梦的不完整的日记。其中有许多地方是谈我自己,因为一个孤身进行思考的人,必然是大部分时间都思考他自己的。不过,在我散步的过程中,在我的头脑里一闪而过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也将在我的记录中有一席之地。我认为事情是怎样经过的,我就怎样陈述,而且,事情与事情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同昨天的看法与明天的看法通常无多大联系是一样的。不过,通过我的头脑在我所处的奇特环境中每天得到的感受和想法的影响,我必然会对我的天性和性格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因此,可以把这些记录看作是我的《忏悔录》的附录,不过,我并不给它们冠以这样的标题,也不觉得还有什么值得用这样标题的话要说。我的心在逆境的洗涤下,已得到净化;即使细心观察,也很难发现在我心中还残存有什么应当受到指摘的倾向。既然我在尘世的爱已完全从我心中消除,我还有什么要忏悔的呢?我既没有什么可称赞的,也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今后,我在人类当中已形同虚无;既然我和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又没有真正可与之交往的人,所以我只能是这个样子。既然我做的好事没有一件不变成坏事,我的每一个行动不是使他人,便是使自己受到伤害,那么,彻底抽身便成了我唯一的选择;我要尽力按我的这个选择去做。不过,我的身虽闲,但我的心还在活动:它还在产生情感和思想。它内在的生命力,似乎由于我在世上的一切利害关系已经断绝,反而有所增长。对我来说,我的肉体完全成了一个累赘、一个障碍,我要及早尽我的所能摆脱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