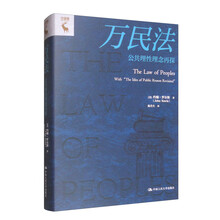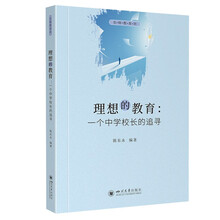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
“9·11”之后的全球化与东亚
卓莫·夸梅·桑达拉姆 著
李佳琳 译,蒋亦凡 校
一个世纪前,主要围绕着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就当代帝国主义问题曾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虽然他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但是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典的著作中,他发现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帝国主义源自资本集中之后出现的寡头或垄断权力,它直接否定了竞争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理想。第二、这种强大的垄断实体所造成的过度的政治影响导致了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主义,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
列宁曾经吸收霍布森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关于现代金融资本(牵涉到银行与工业垄断者的联合体)的分析,发展出了自己犀利的论述,第三国际后来正是因此而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国族忠诚的立场。延续马克思的说法,他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的集中化和中央化的倾向意味着霍布森所说的帝国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演进的结果,而非是霍布森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的畸变。
后来,列宁继续指出,虽然帝国主义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首要的斗争任务是社会主义,但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反帝,却是那些殖民与半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民族解放的斗争可能会带来各个阶层参与的反殖民同盟。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后就提到帝国主义其实是前资本主义的返祖现象(atavism),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而消失。
在当代,讨论帝国主义和帝国的语境已经十分不同。从某些角度来看,二战后的帝国主义与战前殖民帝国已经相当不一样。虽然一些连续性体现在了“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中,但非连续性的方面也被 “后殖民主义”一词的早期用法所承认。
毕竟,战后的美国霸权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冷战格局和马歇尔计划,而非“炮舰外交”或者是其同时代的,或是后来的对等物。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海外扩张历史长达两个多世纪,而从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开始的直接的美国殖民主义本身并不能否认美国霸权的诸多随时间而变化的新的方面。近期学术界从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帝国主义--比如“网络霸权”(network hegemony)和跨国公司共谋--的尝试不应该掩盖美国霸权的不断变化的现实,尤其是从冷战结束后开始的变化。
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同时拥抱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霍布森采用自由主义来反对寡头经济的后果和垄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后两者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否定。所以,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时推行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是两相一致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当代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坚持经济的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却不反对现代寡头企业的出现、整合和政治影响力--这常常是通过对私有产权的强调进行的。因此,从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视角而言,当代经济新自由者可以被认为是不连续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
一些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并非政治自由主义者,尽管近期很多政治的论述总体上倾向于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多人依然坚持政府应该逐渐退出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功能、权力和影响力。然而,很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机构并不坚持自由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声称政治干预并非其职责所在。难怪经济自由主义在种种不自由的条件下被强加于人,结果往往增进了外国企业的经济利益。然而,对于当代经济帝国主义来说,非自由的政治状况并非是必然的,而且很可能恰恰不是它的首选的政治方案。毕竟,基于共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with consent),或者说葛兰西所说的霸权(Gramscian hegemony),通常被认为远比当代殖民主义成本低、问题少。
近期重燃的对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兴趣乃是受到了近期的事态发展的影响。它始于冷战中西方阵营的完胜和现存国家社会主义的显而易见的消亡。这种政治胜利通常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相关联,其中包括对经济自由化的乐观态度,包括那种被称为“全球化”的跨国和跨境的组成部分。这些都会在后文进行讨论。但是,其中最紧迫的冲动则是来自于“9.11事件”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众所周知,这不仅成为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朗的正当借口,也使国际对峙更趋严峻,这部分地表现在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之中。
需要明确的是,单边主义并不是一些评论家有时所说的孤立主义。布什政府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有时摇摆于可欲、可能和可行时的单边主义和不可避免或势在必行时的多边主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种“硬柿子、软柿子”的策略,正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所采用的那样,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为了联合支持布什第二任政府的不同的派别所必须。
而所谓“新保守主义”的阴暗的(即便不是凶恶的)崛起,常在这一语境中被提及。可以理解,“新保守主义者”们自称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拥抱自由民主的政治方案--至少对于中东是这样--并且试图撇清与法西斯主义者的贵族保守资助,以及其他亲美的独裁者和反动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权那里常常见到)的关系。但众所周知,他们从不迟疑于与那些支持利库德党的内塔尼亚胡派的人士结盟。
很清楚,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许多旧的同盟正处于压力之下,联盟或被建起来或被抛弃,以适应新的发展。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的局势给无论是以直接单边主义占领(即便是以那种从未被充分说明的“自愿联盟”的形式)的形式,或是牵涉一些多边管理(比如北约和联合国)的形式进行的帝国主义支配提供了新的合理性。
毫无疑问,国际不平等和支配的藉口久而有之,但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在西方英语国家新右翼霸权的复苏(比如重新燃起的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失败国家”、“吸血鬼国家”、“流氓国家”等说法的热衷),又有了一轮可觉察到的复兴。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原先欢欣鼓舞的福山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调很快就让位于伯纳德·刘易斯-塞缪尔·亨廷顿(Bernard Lewis-Samuel Huntington)关于犹太-基督教北大西洋西方(Judaeo-Christian North Atlantic West,这是一个近期的发明,我们假设它存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的警告。所谓的其他地方当然主要是指当时经济发展迅速、表面上信奉儒教的东亚国家(先是由日本领衔,而后是中国),还有被自己的老阿拉伯罕弟兄轻易断绝关系的伊斯兰教。
我不想停留在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之内,而是觉得有必要回到经济领域,考虑一下近期的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加强或者削弱了国际支配和国际剥削的关系。虽然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并不存在想当然的、简单的关系,尤其是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要大于经济考虑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尽管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依然存活无恙。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要早于当今关于帝国的讨论,并且在此被理解为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和重组的结果。这种关于资本积累的认识,考虑到了其不断变化的特性,它和科技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这样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很明显地受到了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的开创性作品的影响,它也影响了其他人,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这种观点将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或寡头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也认识到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机制和制度在所谓“漫长的20世纪”发生了多少变化。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和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相关,也与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更早期的全球化过程的相关。通过把它确认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将现代帝国主义与早先的与其他经济制度相关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区分。殖民主义的结束,战后的黄金时期,国际经济专业化的巨大变化,各种致力于多边机构建设的严肃的努力,消除国际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发展,都深刻改变了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我在文章的下一部分会谈到,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在国际层面开展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在加强并且深化当代帝国主义。早期的社会危机和劳工运动推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促进了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拓展了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和发展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干预,它们规制了资本积累,但从未破坏它。
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史无前例的。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初期,一些与被霍布森和列宁称为帝国主义的现象有关的跨境流动(比如劳工),其影响力即便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也是相对的意义上要超越当代的流动。的确,这两个时期存在着许多其他重要的差异,但是没有一样能够从根本上否定现阶段仍然具有经济帝国主义特征这一论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