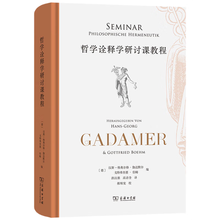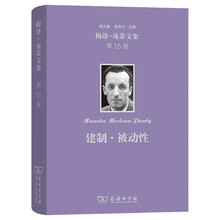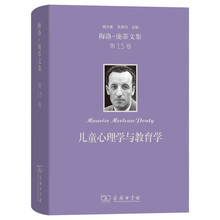痛苦的狂迷和美好的梦境有其不同的众神世界:前者在其本质的万能中渗透到大自然最内在的思想。它认识对生存的可怕欲望,同时也认识到所有进入生存的生物的持续死亡;它塑造的众神,有善的和恶的,与巧合类似,通过突然出现的计划性让人害怕,没有同情心,对美不感兴趣。他们与事实有亲缘关系,并且接近概念:他们很少也很难创作出人物形象。看到他们就会使人成为石头:人们应该怎样与他们共同生存呢?可是,人们也不必与他们共同生存:这就是他们的学说。
那道目光必须从诸神世界转移——假如它不能就像一个惩罚性的秘密那样,被完全揭开——那道目光纵览旁边奥林匹斯诸神世界光芒四射的梦幻诞生:因此,众神形象瑰丽色彩的炽热在提升,而且,真实或者真实的象征性越强烈地发挥作用,其人物形象的感官性就越高。但是,真与美之间的斗争从未像酒神节活动侵入时那么激烈:在这个活动中,大自然揭开神秘的面纱,并且以惊人的清晰性,以那种语气(面对它,迷惑人的假象几乎会丧失其威力)讲述着自己的秘密。这个源泉来自亚洲:但是,它必须在希腊才能汇集成江河,因为,在这里,它第一次发现亚洲无法向它提供的内容,极度的敏感和承受痛苦的能力,与最轻微的深思熟虑和敏锐相结合。阿波罗怎么挽救希腊人与文化整体呢?狄奥尼索斯这位新来的神被纳入美的假象世界,被牵入奥林匹斯诸神世界中:为他牺牲了许多像宙斯和阿波罗这样德高望重之神的荣誉。人们从来没有和一个陌生人费过更大的周折:因为,他还是一个可怕的陌生人(在任何意义上的异乡客人),强大到足以把好客的主人的房子变成废墟。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在所有生活领域中开始:狄奥尼索斯到处渗透,也渗透到艺术中。
观看、美、假象包围着阿波罗和谐适度的艺术领域:这是眼睛的被神化了的世界,是眼睛在梦中闭上眼帘艺术地创造的世界。史诗也想把我们带到这个梦境中:我们应该在睁着双眼时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应该欣赏这些内在的画面,行吟诗人试图通过概念激发我们的兴趣,去看这些内在画面的创作。造型艺术的效果在此被绕道取得:雕塑家通过被雕刻的大理石,把我们带到由他在梦境中看到的活生生的神面前,以致原本作为τελο? (最终目的)浮现的人物形象,对雕塑家和观众来说,都成为清晰可见的,而前者通过雕塑这个中间形象,促使后者去查看:史诗的作者也看到同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且也想把这些形象展示给别人看。但是,他不再在自己和别人之间放置雕塑:更确切地说,他讲述,那个形象如何通过活动、声音、说话和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他强迫我们,对大量的作用追本溯源,探究原因,他使我们需要一种艺术的组合物。当我们看到,这个形象或者群体或者画面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他告诉我们那种梦幻的境况,首先是他自己在这个状态下创造了那些想象,这时,他就达到了其目的。对史诗进行形象地创造,这个要求证明,抒情诗与史诗多么绝对不同,因为,抒情诗从来都不把塑造画面当成目的。二者的共同之处只是某些素材内容,话语,而更普遍的是概念:当我们谈论诗学时,我们并不拥有会跟造型艺术和音乐相联系的范畴,而是两个完全大相径庭的艺术手段的交融混合,其中一个意味着走通往造型艺术的路,而另一个走通往音乐的路,这种交融混合意味着:二者都仅仅是通往艺术创作的途径,而不是艺术本身。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绘画和雕塑也仅仅是艺术手段:真正的艺术是塑造画面的能力,无论这是前期-塑造还是后期-塑造。艺术的文化含义建立在这个特征——一种普遍的人性特征——基础上。艺术家——作为有必要通过艺术手段成就艺术的艺术家——不能同时成为从事艺术活动的吸收养料的器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