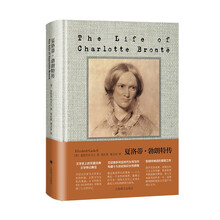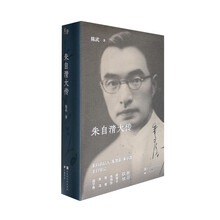珍贵的纪念
邵振国
俞平伯先生赠我的两幅字,我一直珍藏着。
珍藏在我的书房内,未裱,未挂,未曾出示给旁人看过,仅仅与先生赠我的书一起安放在我的书柜内。这是出于我对俞平伯先生的敬重和敬畏,以我的为人,我不会以先生对一个晚辈和孩子的厚爱来炫耀什么,因为那时我的确是一个很无知很无知的孩子,先生作为一代“红学”的丰碑、现代文学史上诗歌散文的巨匠,的确是对一个年少无知的孩子盼其成长进步,才送我那两幅字的。我如今展示出它。也只为证明先生的高尚人品和慈爱,也为我对先生的缅怀,先生已于上世纪即1990年10月15日逝世了。
那是“文革”结束,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距今已显得很远了,那时先生已接近80岁。我是个20余岁的青年,为报考某高校文学系去北京参加考试。此前由于亲戚朋友关系,我们把先生的大女儿俞成叫大姨,自然就把大姨的父亲称呼“外公”。复习考试期间我就住在俞成大姨家。最早她家尚在建国门外大街的一栋楼上,记得那边外国驻华使馆特别多,其他我都淡忘了。后来俞平伯的家才迁到西郊南沙沟的国务院宿舍,就在“七机部”的对面。这两幅字,即是先生在南沙沟住宅楼的一楼那个家中,为我留下的宝贵墨迹,它不仅记录着那位慈蔼、爱人的“外公”,对一个整日埋头屋内看书复习的青年的关爱和希望,笔墨间似乎还浸透着我的青春年华和生命记忆!
大姨安排我跟她的儿子韦柰住一间屋——那是一套很宽敞的、装修设施不错的大三室一厅。大姨说,要不然就让我跟她住一屋了,她每晚都要给她的孙子宁宁陪练小提琴,还要教英语,怕吵了我。韦柰则白天去北京舞蹈学院上班,搞钢琴伴奏,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我有幸多次聆听,我常邀请他演奏,但一般晚间他不演奏,只是笑着朝外公那间屋努一努嘴,是说外公怕吵。如今他已是学院资深的音乐教授了,我也依旧时常记起他弹得极为精彩的钢琴声,那旋律很激情激越,那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我如今想来,它也非常像我的青春岁月!
吃饭在那间大客厅,大家围坐在那张十分简单的折叠餐桌旁。有时外公、外婆也在,大姨说,那就是他高兴的时候,才和大家一起就餐。有时则把饭菜送进他的屋去。我到外公的那间分不清是卧室还是书房的屋去转过几次,既有他和外婆的卧榻,也有他的书案写字台,靠墙立满书架。那间客厅的半周转角也摆着低式书柜,柜面摞满书籍。外公在卧室内常翻阅报纸、看看杂志,有时还能听见他唱昆曲,是那种击节击板的吟唱。我则坐在一边小沙发上默默地听着。我那时尚不会向先生求教什么学问,没有那个能力,虽然我确实已经拜读过《红楼梦辨》,并且还看过他1954年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红楼梦简论》,是我特地从图书馆查找到读的,但是我幼稚得不可能有什么观点或问题提出来。记得有一次聊天时,大姨也在,我刚说出“红楼梦辨”这个词,大姨向我眨了眨眼皮,是怕我勾起外公不愉快的、不愿意说的话题。
但毕竟已是70年代末了,有一天来了两个北大的研究生,事先电话约好来听课,就在客厅里,在那张古旧的餐桌旁,他们请教先生的依旧是“红学”。那天我悄悄地坐在墙角的沙发上,一旁聆听了先生的讲课。授课之后两位学生开出了几张课时费,放在桌上告辞,大姨高兴地说:哈!可以请你去“新侨”西餐厅吃一顿啦!我由此看出,那时俞平伯讲学的机会还非常少而稀罕,使大姨高兴;其二看出先生喜欢吃,尤其是西餐。后来,1985年我结婚不久到北京,便请外公、大姨、韦柰一家人,去了一家很著名的酒店西餐厅,同时邀请了我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汪兆骞老师夫妇在座。就餐时汪老师与俞平伯先生交谈得非常和蔼、投合。
而在我复习高考的时候,我的心情不无苦闷压抑,自己写了一首不堪为诗的东西,至今记得那头两句是:“老去应试学范进,新来拙笔写蹉跎……”不想被大姨看到了,她笑着并拿给了外公。外公不仅看了,还帮我修改了它,让它有点儿像诗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俞平伯没有笑话这样一个落寞无为而苦闷的青年,却鼓励我要“壮怀兴起”,还与一个无知的晚辈一起,“同看前景是青春”!我两手捧着外公赠给我的那幅字,当即就热泪盈眶了。
如今我仍在庆幸,不是大姨把我那几句歪诗拿给外公看,先生不会想起给我写什么励志的字,如是说,是大姨为我“抛砖引玉”了!
另一幅字,我记得是我赴《北京文学》杂志笔会的时候去看望外公和大姨,先生为我写的。虽是“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内容,但我理解俞平伯先生还是为鼓励青年人努力上进,希望他们在文学上取得成绩,报效国家,所以先生依旧写道“同心亿兆巩金瓯”。
岁月如梭,我常拜读先生的著作文集,却很少时候拿出这两幅字来捧阅。时值今天《文艺报》编辑颜慧主任为“收藏”栏目向我约稿,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才捧出它来。它的折叠印痕如同岁月一样留在纸面上,我不知道读者看后会怎样想,而我却又记起了那段对于我的生命之成长弥足珍贵的时光!以及俞平伯先生的高大身影和令人崇仰的品格!
2011年5月12日于兰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