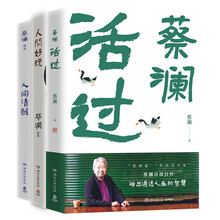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 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 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 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 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 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 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 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 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 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 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 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 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 我名落孙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 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 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 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 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 做了大宫。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 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 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字内 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 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 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 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 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 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 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 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蝮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 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 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 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 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 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 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 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rn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 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人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 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 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 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P2-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