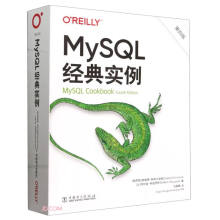永远的萧女孩儿
萧红生于1911年6月,如果她还活着,在我们落笔的这个时刻,她就是一个整整百岁老人了。但是,岁月让她永远以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留在历史中,她是不老的——1942年她在风雨飘摇的香港含恨去世,享年不过31岁,而一部《呼兰河传》,则让读者心目中的萧红更加年轻。
萧红和林徽因都是民国的才女,但如果一定要只选一个作为“民国才女”的代表,我们要选萧红。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她没活到新中国成立。在她生前,她挚爱的国家和民族没来得及给予她与其贡献相称的荣誉,即便是几行伤逝的眼泪都那么少。
如果说林徽因是阳光明媚的大厅里的一株君子兰,那萧红就是北方郊野中的一棵迎风怒放的穿心玫瑰。
无可否认,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舞台虽然在北方,但活跃在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南方人,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等,甚至他们各时期的对立面们也是,如林纾、胡先骕、章士钊、吴宓等等。只有出了萧红,北方人的性格和内心才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中国人整体的心灵史中。
萧红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地方——黑龙江省。多少年了,这里充满着农作的艰辛、大自然和人的漠视,但经过萧红的笔,这里不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那片荒凉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悲欢离合都被点亮了。
读萧红的书,我们有时会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小说,哪个是她的回忆录,甚至我们看的到底是小说还是诗。不过这正是萧红的价值所在,在写作被社会意识形态强烈绑架的时代,她就是一个完全不管不顾的任性的小女孩,她总是直直白白地倾诉给我们在小女孩的眼睛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希望》
萧红确实长大了,却在用一生的时间来回忆童年,回忆祖父怀中的温暖。长大后的清醒让童年的美好更加难以忘却,一想就痛彻心扉。
萧红确实长大了,这个长大的代价太大:
她曾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第一任丈夫汪恩甲的,汪恩甲在二人贫病交加时,把妻子抛弃在哈尔滨的旅馆里。当她的第二任丈夫萧军把她解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出生了,但同样的贫困让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人,从此就是永诀。第二个孩子是萧军的,但又是当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她和萧军分手,带着这个孩子和端木蕻良结婚了,而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有谁懂得一个女人两次失去幼子的苦?
当她带着绝望独自待在香港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可是她这时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是她创作的高峰,同时也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礼。
古人说“长歌当哭”,《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哭,这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孩子最后的哭,只是这哭声中夹杂着她永远不能忘怀的对家乡的思恋。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永远的萧女孩儿
萧红生于1911年6月,如果她还活着,在我们落笔的这个时刻,她就是一个整整百岁老人了。但是,岁月让她永远以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留在历史中,她是不老的——1942年她在风雨飘摇的香港含恨去世,享年不过31岁,而一部《呼兰河传》,则让读者心目中的萧红更加年轻。
萧红和林徽因都是民国的才女,但如果一定要只选一个作为“民国才女”的代表,我们要选萧红。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她没活到新中国成立。在她生前,她挚爱的国家和民族没来得及给予她与其贡献相称的荣誉,即便是几行伤逝的眼泪都那么少。
如果说林徽因是阳光明媚的大厅里的一株君子兰,那萧红就是北方郊野中的一棵迎风怒放的穿心玫瑰。
无可否认,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舞台虽然在北方,但活跃在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南方人,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等,甚至他们各时期的对立面们也是,如林纾、胡先骕、章士钊、吴宓等等。只有出了萧红,北方人的性格和内心才以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中国人整体的心灵史中。
萧红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地方——黑龙江省。多少年了,这里充满着农作的艰辛、大自然和人的漠视,但经过萧红的笔,这里不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那片荒凉的土地,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悲欢离合都被点亮了。
读萧红的书,我们有时会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小说,哪个是她的回忆录,甚至我们看的到底是小说还是诗。不过这正是萧红的价值所在,在写作被社会意识形态强烈绑架的时代,她就是一个完全不管不顾的任性的小女孩,她总是直直白白地倾诉给我们在小女孩的眼睛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希望》
萧红确实长大了,却在用一生的时间来回忆童年,回忆祖父怀中的温暖。长大后的清醒让童年的美好更加难以忘却,一想就痛彻心扉。
萧红确实长大了,这个长大的代价太大:
她曾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第一任丈夫汪恩甲的,汪恩甲在二人贫病交加时,把妻子抛弃在哈尔滨的旅馆里。当她的第二任丈夫萧军把她解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出生了,但同样的贫困让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人,从此就是永诀。第二个孩子是萧军的,但又是当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她和萧军分手,带着这个孩子和端木蕻良结婚了,而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有谁懂得一个女人两次失去幼子的苦?
当她带着绝望独自待在香港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可是她这时却写出了《呼兰河传》,这是她创作的高峰,同时也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礼。
古人说“长歌当哭”,《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哭,这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孩子最后的哭,只是这哭声中夹杂着她永远不能忘怀的对家乡的思恋。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