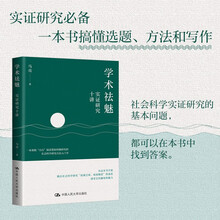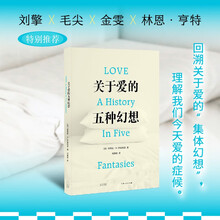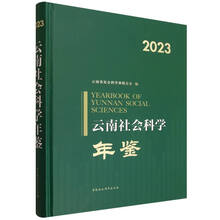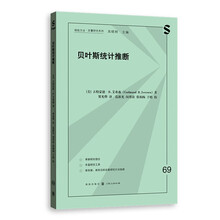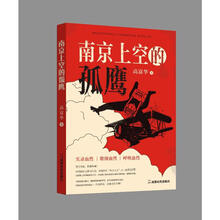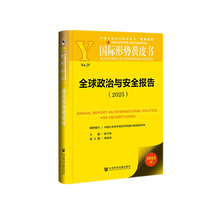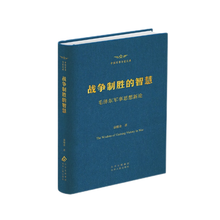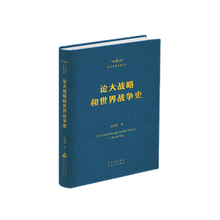过去,文学史家或是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认为“宫体诗”是一种趣味庸俗、有伤风化的“黄诗”;或是受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一文的影响,认为“宫体诗”的最大缺陷,并不在于其描写男女之事,而在于这些作品“没筋骨”、“没心肝”,缺少创作的激情和生命的活力。然而,如果这些作品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表现男女爱情,而恰恰是要通过感官的描写而“因色悟空”,那么它们又怎么可能有活力、有激情呢?与传统的艳情民歌相比,宫体诗是“艳诗”,但却不是“情诗”,因为其对女性体态、容貌的描写虽然细致入微,但却往往不带情感,有一种以我观物的“体物”特征。对此,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受到佛经中注重“观”的结果。在佛教的“观无”态度的启发和影响下,宫体诗人以“无染眼”的体物方式去观察女性的体态、容貌,并进而通过美女之“色”而体悟世界之“空”。于是,在宫体诗人看来,不管是嫔妃、妻妾,还是舞女、歌妓,她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都不过是物象的呈现而已。当然了,“宫体诗”的作者们是否都有这种自觉的佛学意识,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使他们都有这种自觉的佛学意识,是否都能够将其贯穿于创作之中,也还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情况下,保不齐有一些并无坚定信念的“滥竽”会将“劝戒”的调门吹成了“诱惑”旋律,这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从文本分析的角度上看,“宫体诗”中确乎存在着“因色悟空”的佛学痕迹,如梁武帝有《欢闻歌》之一云:“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极郎思,俱期游梵天。”又如汤僧济《咏藻井得金钩》日:“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边。摘花还自插,照井还有怜。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宝钩于此落,从来不忆年。翠羽先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再如王僧孺的《为人述梦》云:“已知想成梦,未信梦如此。皎皎无片非,的一皆是。以亲芙蓉褥,方开合欢被。雅步极嫣妍,含辞恣萎靡。如言非倏忽,不意成俄尔。乃寤尽空无,方知悉虚诡。”细读《玉台新咏》,此类借“色”悟“空”的作品亦不在少数。如此说来,正如美丽的山川景物不过是玄学家言说玄理的由头一样,香艳的金肢玉体不过是佛学家因色悟空的道具。正因如此,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诗作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没有情感,甚至没有欲望的原因所在。正如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云:“法师未通返照,安悟卖花?未得他心,哪知彼意?”总之,在我们看来,“宫体诗”的取材不仅囿于宫闱闺阁,而且模仿佛经故事,因而有写世俗为了勘破肉欲、写女色为了超越情思的佛学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否达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都为重构艺术形象的深层模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的探索,因而是不可一概抹煞的。五 无论是逻辑的结构还是历史的意义,最终都是由具体的艺术家来体现并完成的。隋、唐以后,原来此起彼伏、阶段性发展的儒、释、道三家,却又进入了三教并举、齐头并进的社会环境,这一切体现在诗歌艺术上,便出现了被称为“诗圣”的杜甫、被称为“诗仙”的李白、被称为“诗佛”的王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