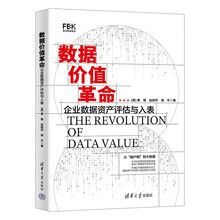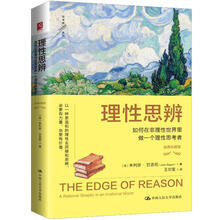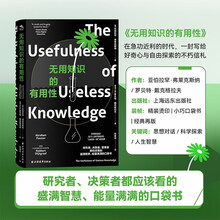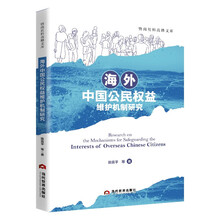前已述及,创办《时务报》使梁启超名重一时,部分即在于其“语言笔札之妙”。对此梁本人后来也有所论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文体问题在当时确是见仁见智,章太炎对此就提出尖锐批评:“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在章看来,“人学作文,上则高文典册,下则书札文牍而已。”高文典册固非人人所有事,书札文牍则未有不用者。“然林纾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这里也道出了报章杂志流行后所引发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办报者如确立面向公众的理念,便不能不考虑表达方式当如何配合。
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辩,值得作为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曾以达尔文与赫胥黎来比喻严复与梁启超,认为推动“启蒙”更有力的是梁启超。所谓更有力,很大程度便是由两人写作方式的区别所造成的。1897年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梁刚走上办报之路,其为文遭到严复的批评,于是梁作了如下的解释:“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征引,便在于梁启超对于在报刊“匆迫草率”发表的文字,也不无遗憾,然而,考虑到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于是又不免“自恕”。而在回应严复对其《古议院考》的批评时,梁又明确指出报刊之文不过是“为中等人说法”:“《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