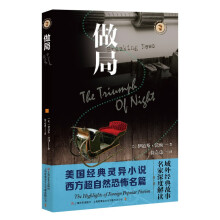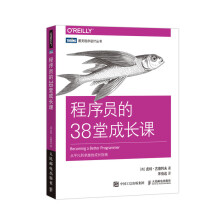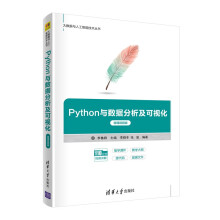要攻击三巨头及其放逐(proscription)政策,其他题目应能提供更好的火力。苏拉这一形象也并非丰满得足以支撑起一种解释。在《纪事》里面,撒路斯特使苏拉成为主角,而在两部政治纪事中,苏拉的角色虽然重要,但不够清晰。撒路斯特在《卡提利纳阴谋》中只略为提过苏拉。《朱古达战争》则没有透露撒路斯特不喜欢苏拉的迹象。而且,为什么马略与苏拉的冲突,甚至在《朱古达战争》这部两人皆有出场的著作中,仍得不到强调?以写作谴责放逐政策的人,应该会发现这场斗争是个诱惑性题目。即使这点得不到承认,似乎仍然可能的是,撒路斯特会做些不详的预告,说说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这二人。那么,为什么撒路斯特避开这个题目,更确切地说,除了最难以捉摸的词语,他甚至没有提到这场即将来临的冲突?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除非撒路斯特另有目的,或者其目的不仅限于隐蔽地攻击三巨头。
这一讨论显示出核心的困难。塞姆的解释过份依赖传记。对塞姆而言,撒路斯特说了什么不如他是谁重要。塞姆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外在于文本的推论性证据之上,而且他不能解释文本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序言。塞姆假设序言大多起装饰或辅助作用,对整体而言仅为次要。这是一项危险的假设,然而,所有对撒路斯特的政治解释的路向,都少不了这一假设。若有人能证明,两篇序言对于各自的叙事部分都至关重要,这一观点的基础就会崩溃。正如我们所知,若文本能以文学的方式解释自身,就既无必要也无理由诉诸作者的外部证据。
概括地说,政治解释所依靠的内部证据并不完备,甚或互相矛盾,其依赖的外部证据则至多只能稍加考虑。因此,必须摒弃此种解释路数。任何作家都不能完全抽身于写作的政治环境,尤其是,作家本人也是政治的戏剧角色。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