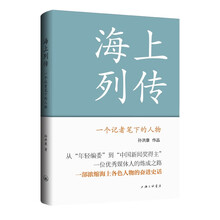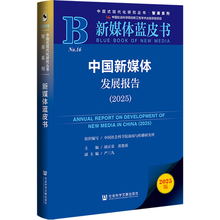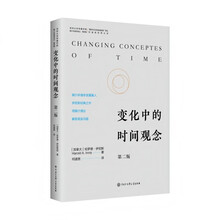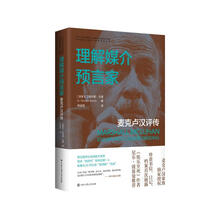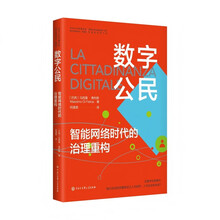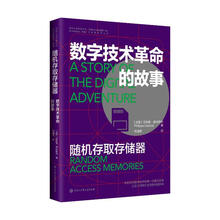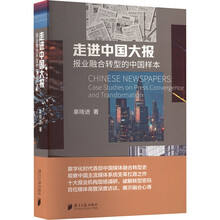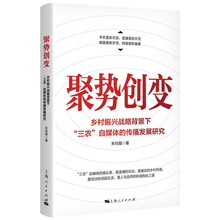民生问题。一向是张元济作为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了建议。他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进餐。宾主畅谈中张元济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凭着一位老出版家、新闻人的经验,提出应设法使下情上达,广开言路;另一条,则是建设必须进行,重要的有交通、农业、工业。他说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穷财尽,现在百端并举,民力有所不逮,关键是要权衡缓急。民生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土地改革。尽管要到1950年1月召开的一届二次政协会议上中央才将土改问题提上中心,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土地改革日益明显的矛盾与冲突要在以后才逐步凸显出来(袁小伦《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一文对此有详述,刊《书屋》杂志2002年第8期),但类似的冲突在1949年里就已经出现苗头了。9月16日,张元济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来访的河南第一师范副校长高镇武所说:“自言年七十矣。……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口栖止。”晚上陈毅与梅达君来访,聊天时陈问及张在北京的旧友今存几人,受高镇武之事所触动的张元济就向陈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引者注:傅与陈毅同为川人)。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伊问为某军队所占,昔为国民党军,今则不详。”陈毅答复说“当查明,为之设法”(9月16日记)。9月27日,他接到远在南方的藏书家刘承斡来书,告诉他说南中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部队占用。刘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1949年10月30日致刘承斡)此事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10月15日学者孙楷弟来,也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读到这样的日记,我们不能不佩服张元济这位阅世丰富的长者对时势与气氛敏锐的洞察力。他所记下的并非特殊现象。袁小伦在上引文中说:“总体而言,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句常用话讲,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当时与张元济一同与会的另一位老民主人士柳亚子,常常是“牢骚太盛”,令他牢骚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断昕到自己故乡为关于房产、土地之类的求援之声。宋云彬1949年7月24日的日记记道:“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冷眼红尘》第143页)柳亚子虽说能“识大体”而对这类频传的呼声“置之不理”。但无疑,这增添了他们作为一个“叹息肠内热”的知识分子对民生作出本能的关切。张元济本人故乡是否有此遭遇,从目前所见资料无法论定。上述王云五《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