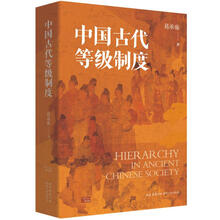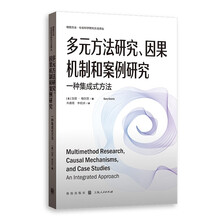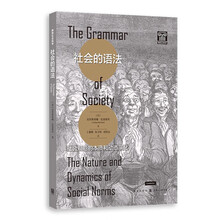在报告开始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21世纪初期语言和国际化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在冷战期间(经过改进的)所使用的语言和策略并无太多的区别,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因本国出现的安全问题和经济需求所必需的学术专业思维。对于最初为了应对战时和冷战期间的敌人所设计的知识生产场所和文化分类的持续依赖仍旧是一个当代国际化话语令人困惑的特征。这些观点已经成为一个深的印记明显体现在布朗大学国际委员会一个名为“和世界接洽”的报告中,在该报告中区分了布朗大学已经建立联系但是还可以加强联系的五个世界范围内的区域:非洲、中国、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①这些标签再现了一个战时建立世界秩序的一个过于简单的对策,并且这个对策赋予了美国视点以特权,这一点我将在随后的报告中详细的阐述。而有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和经济支持,这种类似的分类随即变成了整个国家创建地区研究系和项目的组织纲领。在随后的50年,地区研究系和项目对于美国学生了解除自己国家外的其他文化以及学术领域和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或者缺乏联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近来高等教育学院对于国际化的热情所证实的那样:地区研究模式同样也影响了大学管理者如何应对复杂的全球化进程。
教职工的发展程度、项目的发展以及我们所有希望可以国际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将在大学管理者所建立的分类中进行。难道这一切不能让我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分类本身是否会有问题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地区的定义本身在历史层面、语言学层面和文化层面都不太有道理,而且更在于人们仍在不加批判的运用它,或者说对于知识生产的框架没有过多的进行研讨。
我的这个报告和我的布朗大学同事们的视角有一点不同。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和人文研究合作项目希望在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话题上有全新的合作和交流。正如伊丽莎白·韦德(ElizabethWeed)、王玲珍和麦克尔·施泰因伯格(MichaelSteinberg)在报告里所指出的那样:作为需要探索的领域,不管是性别研究还是人文研究,都急切地需要共同的合作和努力。考虑到对于“地区研究”命运的激烈争论以及在美国学术界对于“国际化”的含义的争论,我希望借我的报告提出我们正在探讨的合作方式以及学术研究问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