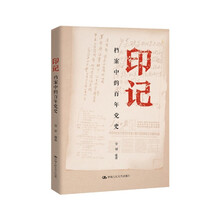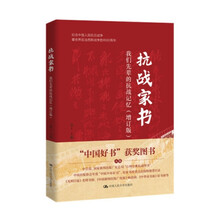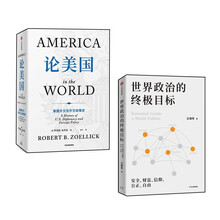一、40年代末50年代初,燕京宗教学院的
去留问题和办学问题
我是1944年第一次认识赵先生的。当时我在日伪的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二年级读书。赵先生的朋友陈伟岷(我叫她“姑姑”)是圣公会的教徒,与赵先生很好。她带我到南沟沿圣公会去见赵先生。他刚从日本的监狱出来不久,住在圣公会写《圣保罗传》。陈姑姑曾跟我说了好多赵先生的事迹,我现在具体记不起来了,当然讲了他在狱中的事迹以及他对基督教的贡献等等,使我对他产生了崇敬的心情。
那次见面以后,很长时间未再见,直到我去燕京宗教学院赵先生门下读书。我与刘清芬、杨周怀、程紫明、张秀一班。我是在赵先生1948年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阿姆斯特丹会议时入学的,比同班同学晚来半年,他们读了三年,我读了两年半。赵先生允许我与他们一起于1950年夏毕业。1951年8月,赵先生给我证婚。他大概给很多人证过婚,我是最后一个。
40年代末5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对于宗教学院来说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作为宗教学院的院长,赵先生更是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要在时局巨变的关键时刻,对学院的出路做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个人的命运,还有我们这些学生的命运后来都与此密切相关。(当然再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不是他所能掌握得了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