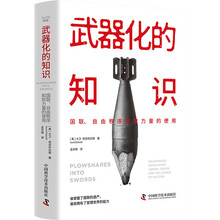外国街道与中国街道 伦敦的街道都伟大得很。他们从这一块地方通到那一块地 方。你便用了他从这一块地方去到那一块地方。他们象征一个起 点,一个终点。为住在伦敦的人,街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 所系联的两个地点。他们从家里走到店里或是办公处里,待忽再 回到家里。街道的责任便是去让一个人走到他所要去的地方。这个,我想,便是伦敦的街道和大陆诸国的街道不同的地方。在法兰西,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你是简直生活在街道上的。你在街 道上造谣言,谈政治,调情,偷懒。你在街道上吃饭喝酒。你在上 面消遣你的日子。你更坐在那里对着它望,像在电影院里望着银 幕一样。你可以看见几千百出戏;他们可以叫你笑,可以叫你心 跳。人们又都在街道上装腔,作势,高谈,低语,像在舞台上也像在 游戏场里;你可以参加也可以在旁边观察这些小情小节。在法国,街道是一切结合的泉源,它把所有在上面走过的人都带到生命的 河流里去。这两段话是一位法国女作家到伦敦去旅行以后,在一本书里所写 的印象。她虽然是描写英国和别国的人对于街道关系的不同,但是英 国及别国的民情国情的分别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了。英国人刻板的生 活,和法国人活泼的趣味,都从他们对于街道的关系而显示的清清 楚楚。当然,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和街道发生关系的:没有街道(在此地 包括一切的行径),人和一切的关系都会断绝;没有街道,也许便没有人 类。所以从街道上去观察一切人的活动,是不会失望的。一位闭户读 书的学者不及一位沿路探访的新闻记者了解世故人情,便是因为前者 和街道太疏远了。那么,从中国的街道,我们能看见些什么呢?凡是我们中国人,凡 是曾经在街道上经过的,我想都应当能回答这一个问题吧?不过有些 人会说,上海的街道和内地的不同,内地的街道有时会没有人。以我的 家乡余姚来讲,它在内地是比较活泼的城市,但据说它还保存些古风。一出门便有几只对你摇尾又像会咬你的野狗(前年回去扫墓,看见有几 个警察拿了竹竿把它们沿路一只只打死,据说防疯狗,又据说用竹竿是 为了省枪弹);走几步就有粪缸,经过的时候,一群苍蝇就满天飞,有几 只会紧跟在你后面厮缠不清;脚下的石板有些是活动的,不留神会摔 交;走了不多时,后面就又会跟着一群乞丐。在苏州,有一群驴夫会把 你抱到驴背上;在杭州有一群船夫会把你拉进划子里。那位法国女作 家要是来到中国,我不知道她会写些什么文章。我是生长在上海,又是居留在上海的;对于上海的街道当然知道得 更详细;让我把上海的街道和我的关系讲一讲,也许可以回答上面的 问题。在我回忆里,我第一次知道和街道发生关系,大概还只三岁。记得 女佣为我洗好脸,换好衣服,就把我带到祖母跟前。祖母手里早拿好了 一个黄布包,为我挂在胸前;又在我眉心里用挖耳头染了一点胭脂。(黄 布包里是一本经咒,点胭脂也是避邪的)。又对我说,到了外边不要乱 跑,乱跑了有“陌陌人”会把我抱去,那次好像到一家亲戚家去贺喜,到 了那里女佣总把我抱在手里,否则也总把我的手拉紧;回家的时候,那 位亲戚给我一枝安息香,一路上女佣只是拍着我说:“乖宝宝,居居哉,弗要吓,乖宝宝,居居哉……”从此我听到上街去总觉得好像是冒险。长大了,祖母一天到晚只是查问我们一班孩子,就怕我们溜上街去。她 又时常警告我们,说小孩子不能出去,外边全是拐子,他们会念咒语,对 我们念了咒语,我们就会失去知觉,我们会看见左右是两条河,后面一 头奔上来的老虎,我们就会望前逃,一直逃到拐子的家里。她越是说得 可怕,我越是觉得街上有趣,时刻想出去看看这些奇怪的事情。终于有 一天,得了机会一个人走出了后门。那天正是新年初二,天已快黑了,我口袋里带了许多月炮,看见人家的孩子都在放着玩,便自告奋勇加入 了。忽然有一辆黄包车跑过,上面坐了个外国人,月炮放在空中,下来 恰好掉在他身上,他竟然像头受了伤的老虎,大叫一声,跳下车来,捉住 我的领口,重重地在我后脑打了一下。以后虽然有我的教师听得信息 赶来和他讲理,虽然那个外国人在到捕房去的路上溜走,可是我受的侮 辱永远也不会忘掉,同时对于街道的印象又坏了一次。以后读四书了,先生讲到孔子的功绩;据说孔子治国不到三月,百 姓即“路不拾遗”。他又说可惜孔子治国只有三月便被奸人赶走了。我 从此就觉得现在的街道上都是沿路在拾着人家掉下来的东西的人。当 先生教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的时候,我总想“三人行必有我贼也”来 得更合时宜。过后又听人说:“上海遍地是黄金”,同时又看见人沿街在 拾香烟屁股,于是更确定了我“世道日衰”的信念。人一天天长大,虽然祖母管紧了不准出门,可是从家人口里传来的 街道上的消息,总是什么快马车翻身了;某某人让巡捕捉去了;什么宋 教仁被刺了:所有的新闻,都是在证明街道上的危险。等到自己学会了开汽车,更觉得路上的人时时刻刻像在逃难。在 路上好像每一个人都想独出心裁发明些走路的样子:有的走在路中东 张西望装出一种看风景的样子;有的拖老带小像跳舞的样子;有的突然 地从路边跳出来像变戏法的样子;有的低头缓步像哲学家的样子;有的 走一步退一步像和你玩“老鹰捉小鸡”的样子;有的像在地上找东西的 样子;有的又好像要和汽车头决斗的样子……样子实在太多了。记得 前年有一位墨西哥画家到上海来,我们无意中谈起各种动物在汽车前 穿马路的样子。他说,晚上开车看见前面的猫最可怕,远远地你只看见 两粒绿光,等你走近,它一闪就好像钻进你的车底下,等你赶快停车,它 却早已等在路边了。他又说,狗也特别,它们或是站在路边,或是站在 路心,起先并不动,等你走近,它就直打你车前冲过去。他说最奇怪是 鸡,譬如它要从路左穿到路右,等你走近,它一定嘴里装出一种急叫,穿 过去可是不到路右总又马上退回来;据说鸡的后面是拖着一根生命线 的,它怕你会把那条看不见的线压断。我便觉得上海的穿马路人又像 猫,又像狗,又像鸡。我总不懂天底下为什么有这种为要早到对街一秒 钟而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其实到了对街他一样地还是看风景。我这些当然是坐在汽车里说的话;走在路上反过来又会觉得汽车 像老虎,它只想吃人。“他们已经比我们快几十百倍了,他们还要开足了 速度,又不是去赶死!”这是当我们走到路上骂坐汽车的人的话,还有街 道上那种“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的牌子,那是给走路人的警告。而 坐在汽车里的人,有几个又像犯人一样,左右前后有武装的保镖,好像 满街都是强盗。所以我说,假使有人要问我上海的街道,就连内地的街道;我一定 说:“危险!”选自1935年《时代画报》第8卷第7期“时代讲话”专栏 P23-26
展开